腳踏車與糖煮魚 | 運動資訊第一站 - 2024年1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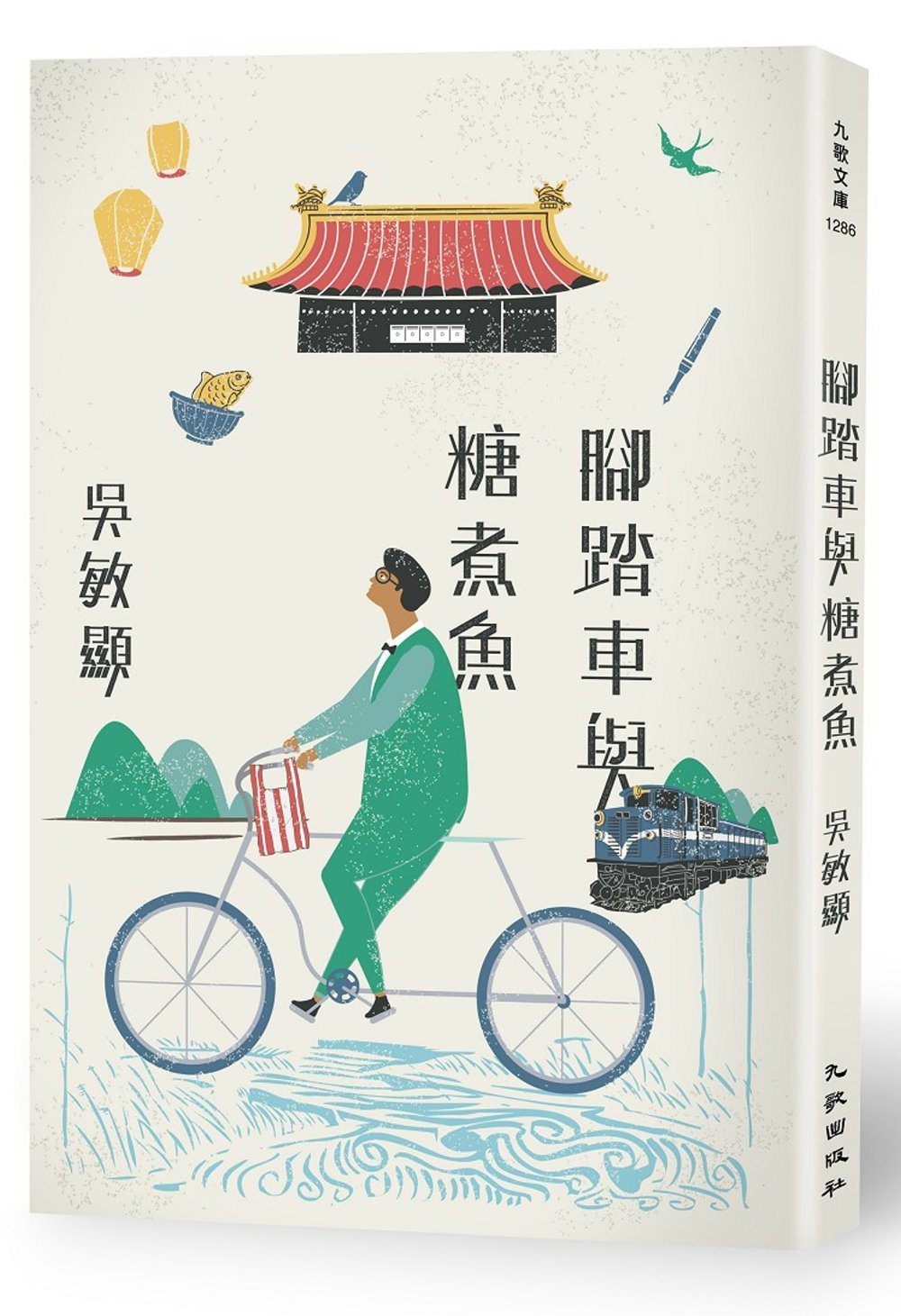
腳踏車與糖煮魚
張曉風:「我喜歡分享吳敏顯這個『記錄人』極其認真極其翔實而又極其細膩多情的記憶。」
在山海環伺原本翠綠的田野,有我永遠挖掘不盡的礦脈。只要我繼續寫它,任誰去填平稻田溝渠,任誰去蓋豪華農舍,鋪再多的道路,砍除再多樹木竹圍,我還是能夠從記憶中去填補存真。——吳敏顯
蘭陽平原是哺育吳敏顯成長的故鄉,這裡的溪河溝渠、風土人情,不啻是他尋常生活的風景,也是他的心靈原鄉與創作來源。他大部分的散文或小說,都以這片土地作為舞台,《腳踏車與糖煮魚》,還是以素樸溫厚之筆,描繪回憶中已不復存的老街景、熟悉的鄉民、填平的河川稻田、被遺棄的神仙與老祖宗……
作者召喚久遠的影像,栩栩重現日治時期〈那一年半載〉,貧窮匱乏的婦女背著嬰兒「跑野米」貼補家用,可愛奶娃以另類的方式參與抗日;漁村孩童輪番學騎村裡第一輛腳踏車,準備長大後載新娘子回家,以及吃過便惦念難忘的里長的糖煮四破魚,拼貼成北部濱海公路上純樸的漁港風情畫。回顧單純動人的往事之餘,吳敏顯不忘活在當下,以幽默詼諧的筆調,刻畫現代人如何周旋詐騙電話,應對一則則「寂寞芳心等你來電」的簡訊,追尋被歲月塞爆而走失的記性。
過往的人事流轉,在吳敏顯的記憶中,散發出珍珠般璀璨的光輝,而現在的日常浮想聯翩,經由他真誠的書寫變得有滋有味, 像吃盤生菜沙拉般新鮮爽口, 於嬉鬧妙語中閃現人生智慧。
本書特色
★幽默趣味的在地書寫,親切易讀的日常散文
作者簡介
吳敏顯
台灣宜蘭人。曾任宜蘭高中教師,《聯合報》副刊編輯及萬象版主編、宜蘭縣召集人,宜蘭社區大學講師,宜蘭縣文獻委員會委員。
著有散文集《靈秀之鄉》、《青草地》、《與河對話》、《逃匿者的天空》、《老宜蘭的腳印》、《老宜蘭的版圖》、《宜蘭大病院的故事》、《宜蘭河的故事》、《我的平原》、《山海都到面前來》;小說集《沒鼻牛》、《三角潭的水鬼》、《坐罐仔的人》等。
作品曾獲選入國立編譯館《國中選修國文教師手冊》、宜蘭縣政府《鄉土語言教材》、台灣北區五專聯招國文科試題、全國語文競賽國中組朗讀篇目、中正大學語文研究所試題、文建會全國閱讀運動文學好書,及《華文小說百年選》、《聯副三十年文學大系》、《中國當代散文大展》、《中國現代文學年選》、《中華現代文學大系》、《台灣當代散文精選》、《台灣藝術散文選》、《台港名家散文精品鑑賞》、《年度詩選》《年度散文選》、《年度小說選》等。
●卷一
那一年半載
牙仙寶盒
尋找或遺忘
狙擊手
分身
●卷二
田野的光璨
樹屋
波光
冷天的陽台
自己的影像
●卷三
永遠是我的城鎮
神仙隱居的村落
寂寞的老祖宗
雜貨店
耳聞目睹
●卷四
三峽四疊
紅瓦牆
腳踏車與糖煮魚
舊居
聽石獅子說話
後記
後記
閱讀的樂趣
三百多年前,張潮在《幽夢影》寫說:「讀經宜冬,其神專也;讀史宜夏,其時久也;讀諸子宜秋,其致別也;讀諸集宜春,其機暢也。」把讀書的要訣與享受的情境,做了非常精闢的剖析。
我寫了幾本散文和小說,從來就不知道該建議別人什麼時候讀它才適合,因為這些文稿既沒有經史子集那般深厚的學問,更禁不起推敲考證。充其量,不過是一個筆耕幾十年的作者,真誠地描繪出自己日常的浮思遐想與周邊見聞,讀它大可不忌春夏秋冬,不避晴雨寒暑,廚廁車床隨處坐臥,皆可翻閱。
可惜近年來樂於閱讀書籍的同好,越來越少。無論讀本出自古今中外大師嘔心瀝血創作,或歷經歲月淘滌而留存的名著經典,往往不如網路上一則笑話或一幅漫畫來得討喜受歡迎,更遑論現代人書寫的散文和小說。任何人寫出文稿編印書冊,想覓得知音,都要有自知之明。
其實在電腦網路發明之前,讀書除了應付升學考試求職,會把它跟唱歌、遊戲、打牌、喝酒等諸多嗜好併列的,並不太多。二十幾年前,我寫過幾則有關閱讀的真實故事,正好用來證明個人絕非信口開河。
故事之一:帶尺來量
在宜蘭市區開過書店的郭小姐,營業期間曾把店裡庫存的一套遠景版諾貝爾文學獎全集精裝本,搬到羅東書展會場以二點五折低價陳售,展示幾天乏人問津,迫使她分冊零賣。果然,一口氣就賣出三、四十本。
我得知消息趕去選購時,卻發現個怪異現象。其中,蕭洛霍夫四冊的《靜靜的頓河》,竟然只剩第一冊和第三冊;湯瑪斯曼上下兩冊的《布登勃魯克家族》,也僅存上冊孤單的留守,令人百思不解。探究原因,竟然扯出一段買書人拿尺來量的故事。
話說前一天店員輪班看場時,來個衣著不俗的士紳,瞧見這套紅色封面又燙金圖案的精裝書,認為買回家擺進新裝潢的客廳壁櫥裡,和收藏的洋酒放一塊兒,肯定氣派搶眼。細問每本價格竟然只要幾十塊錢,等於稱斤買賣,馬上從口袋掏出一條兩頭打了結的塑膠繩,橫在書架上左右比畫,準備買個幾十本回家當擺設。
當他發現塑膠繩末端那本書厚度超出繩結,就從中間挑出一本稍厚的書冊挪到比畫範圍外,然後找本較薄的替代。一次不盡理想,便行抽換,直到所挑的三十來本精裝書總厚度符合那打結繩索的長短,立刻付錢裝箱帶走。
面對這樣的結果,郭小姐哭笑不得地頻頻向我致歉。我安慰她說,對方買回去的畢竟是文學經典,多少能在家裡散發書香,比起某些拿彩印的書牆影像壁紙逕往牆壁貼,要實在得多。
故事之二:電話簿也算藏書
有個老鄰居到一所國中任教,她希望教室內充滿書香氣氛,方便培養年輕孩子讀書習慣。即規定班上每個學生必須帶三本課外書到學校,做為班級圖書館藏書。等學期終了,再各自取回或與其他同學交換。
按她估計,班上四十名學生,每人三本,全班就有一百二十本課外書,扣掉重複部分,每個學生每學期至少能讀到幾十本甚至上百本的課外書,喜歡看書的孩子整個學年下來,就可以讀一兩百本課外書。
她想,這樣的安排絕對能夠養成年輕孩子閱讀習慣,從書香薰陶中改變氣質,增進學識。
等班上學藝股長把書收集得差不多,她才發現,縣政府和鎮公所印發的《農民曆》就有三十幾本,高居榜首;其次,地區農會編印的《農保手冊》、《農藥使用須知》,電信局編印的《住宅電話簿》、《工商消費電話簿》皆被當作班級叢書。大槪只有零星幾本雜誌、故事書、漫畫書和言情小說,勉強算是課外讀物。
學藝股長見老師愣在那兒半天沒說話,便吞吞吐吐的向她報告,本來還有同學交來幾年前印的農民曆和電話號碼簿,全被他退回了。
她把一些交農民曆和電話簿充數的學生找來,問他們平日身上有沒有零用錢,家裡為什麼連一本課外書都買不起?
多數學生的答案是,身上的確有幾十塊到百來塊可供花用,但他們每天要喝飲料、吃零嘴,星期六下午及星期天還要看場電影或到遊樂場玩耍,這點零用錢根本不夠花,哪來錢買書?
故事之三:班級書箱
我還有個朋友早年被派到冬山鄉下小學擔任校長,當時學校沒有圖書館,他就想出窮人家的克難辦法,請老師們分別到羅東街上一些雜貨店去要來裝肥皂用的木條箱子,刷洗乾淨後發給各班充當「班級書箱」。再由學校和家長會籌錢買書,希望孩子們有機會多讀一點課外書。
過沒多久,校長卻發現班級書箱裡的書經常短少。想持續為同學添購新書,在這鄉下學校可是個大負擔,要計畫很久且得到處省錢湊合始能如願。
他只好要求各班級任導師,鼓勵學生讀書時縱使把書本讀舊、讀破,也不能把書讀丟,讀得屍骨不存,教後續想閱讀的同學沒書可讀。校長同時和學生們約定,哪個班少掉哪幾本書,便由那個班同學負責買來賠償。
這位校長朋友告訴我,等到學期終了逐一巡視後發現,大部分班級書箱的書儘管一本不缺,完全符合他的要求。但整箱書籍,竟然嶄新如初,書頁裡外連個小手印都找不到。
重述這三則老故事,讀者朋友不難明白我的意思。
現在社會多元,任何人不能只站在自己的角度看人。何況已經少有家庭把書架書櫃做為必備的家具去設置,那些擺洋酒的客廳大概也不做興間雜幾本書冊,更不知道還有多少校長老師願意為孩子們籌設班級書箱,鼓勵孩子多讀點課外書。
如果有,作家寫書出書還有機會充當門面,直等到書冊裡長出霉點黃斑這段歲月,多少總有一絲希望:在其中某一天會遇上知音。
和朋友聊天,只要談到寫書讀書,我都不忘提醒對方,如果讀了還能認同,就請推介給同好。若翻個幾頁,仍然引不起興趣,那就轉送給其他朋友。
把買來的書它當成一張賀卡、一束花朵、幾粒水果、半打飲料或一盒餅乾送人,算是為書找到好歸宿。多少可以幫所有作者,減輕為印書而砍樹造紙的罪過。
讀書的樂趣,有時候像攬鏡自照,有時候像推開一扇窗子面對風景。每個人不但能夠保有原本的自己,又可以去探索尋覓書中更多的知音,與作者分享現實生活的煩憂和喜悅。這也是書籍寫作者樂於追尋的。
以上是今年一月我在《文訊雜誌》刊登的文字,就充當這本書的後記吧!
《腳踏車與糖煮魚》裡的二十篇散文,是近兩三年來發表於各報刊的文稿,自認為寫得認真誠懇,應該值得一讀,應該能夠讓大家讀出一些趣味。
那一年半載 我出生在台灣東北部的偏僻鄉下,一歲半以前的生活空間,正值日本統治末期。所有對日據時代的認知,幾乎全來自長輩們口述,外加長大後讀到的書本及報刊。就一個姓名曾經短時間登錄日本戶籍冊頁者而言,對那個時代的了解,也只能從這些途徑去領略感受。 我出生的村莊,位於宜蘭平原靠海的壯圍鄉下,它同時是我生長了大半輩子的天地,鄉人大都種田或做工。 如果有人想離開這塊平原,往南走可經蘇花公路到花蓮、台東,那片比宜蘭更荒僻的後山。而朝北走可以到台北大都會,但必須在大山裡繞得暈頭轉向;或者搭硬板凳的火車,穿行一座座黑忽忽地隧道。 在我小學畢業以前,絕大多數鄉親不曾離開過這個三面被高聳連綿山脈環抱,一邊滑落太平洋的平原。 地處窮鄉僻壤,鄉人想活下去,除了吃苦耐勞,就是撐滿肚子苦水自得其樂。這種子民,正是統治者眼中的順民、良民。 當然,有少數腦筋奸巧的,會竭盡所能去巴結諂媚日本人,搶先把自己和家人姓名改得像日本人,自以為從此高人一等。 我的家族繁衍到父親那一代,他是唯一讀完小學懂得看書寫字的,不改名不改姓地到日本人經營的二結製糖會社工作,在載運甘蔗小火車的「二萬五車站」(現今宜蘭縣三星鄉萬富村),擔任原料蔗甜度抽檢工作,結婚後回到離家較近的壯圍庄役場(即壯圍鄉公所前身)當辦事員。 日本主管好意勸他,說如果改個日本姓名,對職務升遷與物資配給都有好處。縱算顧及親友鄙夷,不好將自己改名換姓,照說不難幫我這個剛出生的長子,取個日本味名字。例如:吳太郎、吳一郎,或叫一雄、正一、健一之類,但父親並未這麼做。 後來我進小學,曾羡慕取這類名字的童伴,他們名字用閩南語喊起來,比敏顯兩個字響亮得多,用漢字寫出來筆劃也簡單多了,不像我動不動就會把手腳伸出練習簿的格子外,稍加克制,則緊縮成一團糾纏打結的線球。 在那個男尊女卑年代,連女孩子取名都有類似傾向,身邊不乏取名月子、美子、惠子、秋子、春子、梅子、芳子的童伴。子字日語發音「課」,直到台灣光復好些年,鄉間四處還聽到這個課那個課地課來課去,叫喚彼此。
 BiCYCLE CLUB 國際中文...
BiCYCLE CLUB 國際中文... BiCYCLE CLUB 國際中文...
BiCYCLE CLUB 國際中文... 自行車健康享瘦
自行車健康享瘦 BiCYCLE CLUB 國際中文...
BiCYCLE CLUB 國際中文... 自行車設定:設定就是踏入運動型自行...
自行車設定:設定就是踏入運動型自行... 運動自行車的選擇與騎乘:最自由的移...
運動自行車的選擇與騎乘:最自由的移... BiCYCLE CLUB 國際中文版72
BiCYCLE CLUB 國際中文版72 愛上安心騎:自行車生活禮儀與安全騎乘指南
愛上安心騎:自行車生活禮儀與安全騎乘指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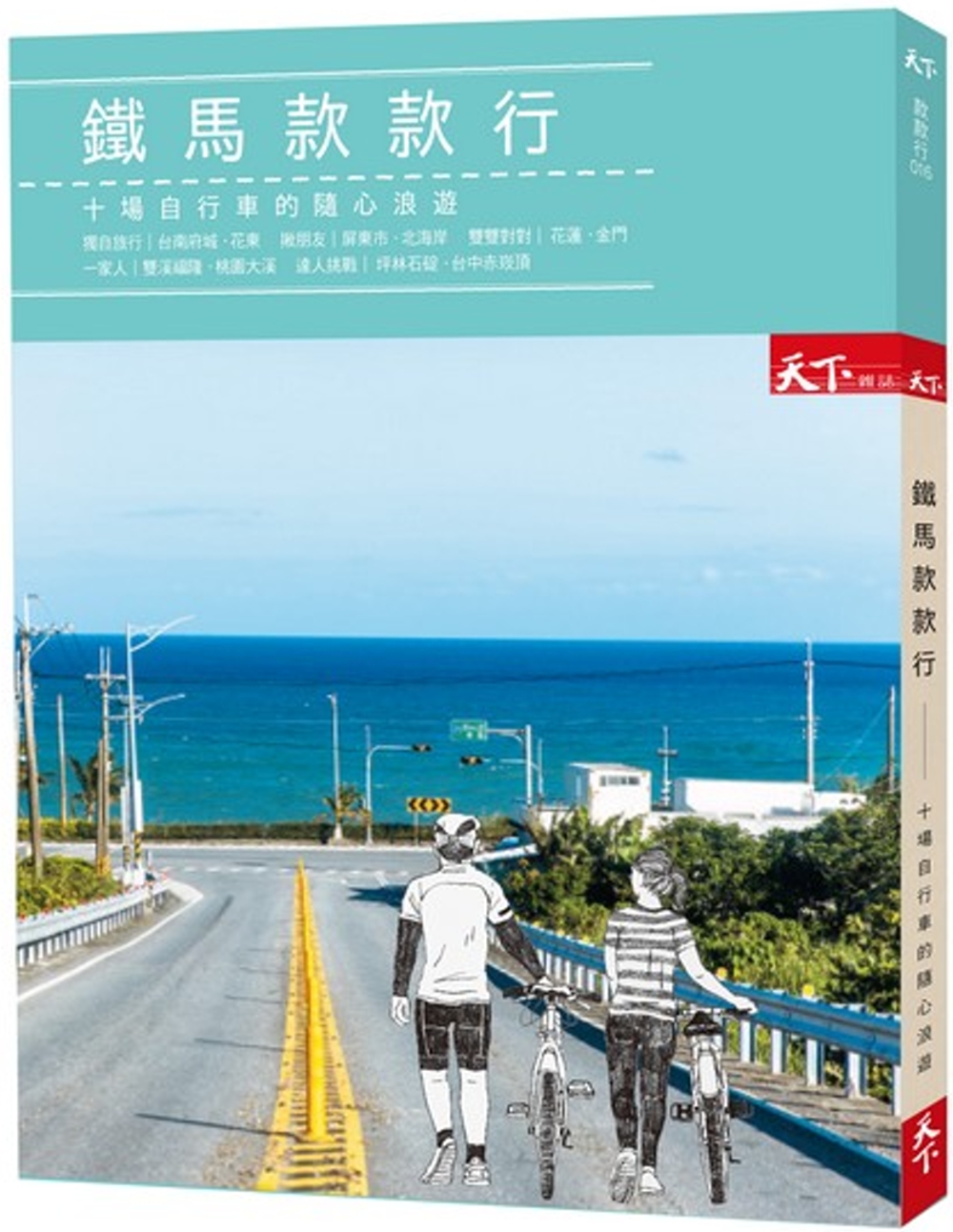 鐵馬款款行:十場自行車的隨心浪遊
鐵馬款款行:十場自行車的隨心浪遊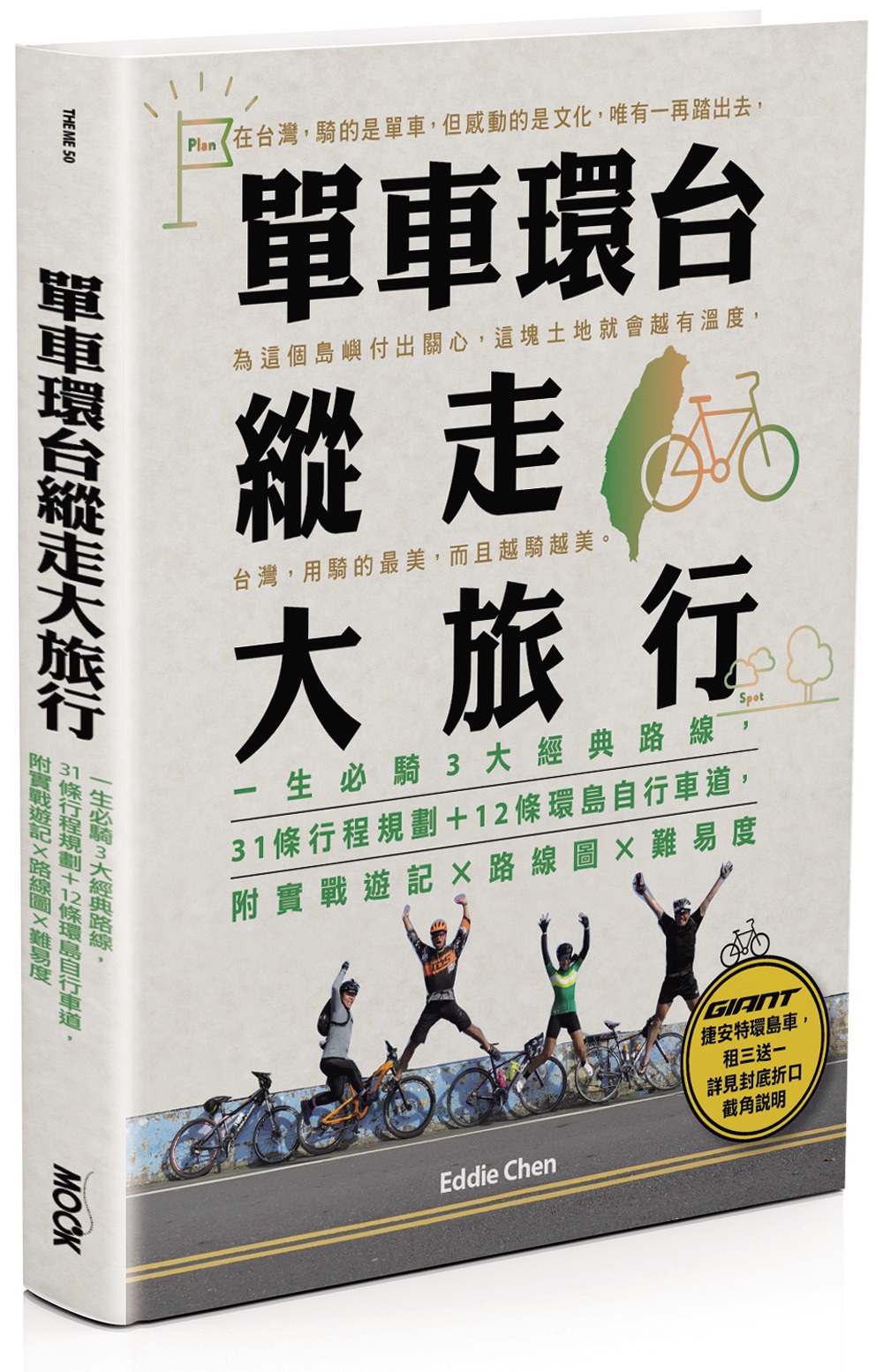 單車環台縱走大旅行:一生必騎3大經...
單車環台縱走大旅行:一生必騎3大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