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母峰史詩 | 運動資訊第一站 - 2024年1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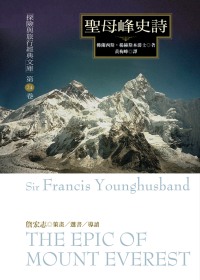
聖母峰史詩
在生命中,知識並非一切。科學可能滿足了,靈魂卻不。促成這樁事業的,是人的精神,而非科學。精神永遠不能安息,除非它完成了自己。
──佛蘭西斯.楊赫斯本
一九二四年六月八日,英國聖母峰探險隊隊員喬治.馬洛里和安德魯.厄文做最後一度嘗試登頂。從英國出發前,有人問馬洛里為何在失敗兩次後還打算登頂,他做了句有名辯辭:「因為山在那裡」。這兩個人「最後一次被看見的時候,正矯健地往山頂攀登」,之後他們消失了……。
直到七十五年後,一九九九年五月,馬洛里凍得像雪花石膏般的屍體,才在聖母峰高聳入雲的斜坡上被尋獲。但他身上沒有照相機,沒有筆記,沒有任何證據可顯示他們倆是否早在紐西蘭籍登山家希拉瑞(Sir Edmund Percival Hillary, 1919-)和雪巴嚮導丹增成功攻頂前三十年,就已經登上聖母峰頂,是否創下了世上首次登上世界最高峰的歷史紀錄……。
楊赫斯本這位攀登聖母峰的提倡者和慫恿者,英國皇家地理學會聖母峰委員會首屆主席,在一九二六年代表聖母峰委員會撰述此書,記述下英國在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和一九二四試圖登上聖母峰峰頂的嘗試。他以真實的角度審視整個事件的原委,完美書寫出這些登山行動整個過程的真實場景,並不偏不倚為這些英勇的功績留下紀錄──那個時代,水土適應的極限及持久缺氧的結果,科學上所知甚少,更還沒有衛星電話、全球定位系統、直昇機、保暖雪衣,以及地圖的指引。這些不平凡的靈魂,無疑達成了早期登山探險成就的極致,也證實了人類挑戰挑戰極限的無畏勇氣。
作者簡介
佛蘭西斯.楊赫斯本爵士(Sir Francis Younghusband, 1863-1942)
中文名榮赫鵬。英國軍官,也是十九世紀最著名的英國探險家之一,旅遊範圍多在印度北部和西藏地區,對地理研究方面貢獻良多,二十四歲時曾經隻身穿越戈壁沙漠,還曾發現一條從中國通往印度的新路徑。
一九○三年,他曾帶領一支軍事探險團進軍禁城拉薩,迫西藏統治者達賴喇嘛於一九○四年九月六日簽訂了「英西藏條約」,為英國贏得希冀已久的貿易條件。這個行動使他在一九○四年榮獲騎士勳章。
這位帝國時代軍人同時也是位運動健將,曾經保有三百碼短跑世界紀錄。他也曾致力於籌組探險團,從事人類歷史上頭幾次的聖母峰攀登嘗試。此外,他還是位作家,更在入侵西藏後,彷彿獲得天啟般放下帝國主義的屠刀,在晚年成為宣揚藏密的神祕主義者。
一九四二年七月三十一日,他在英國逝世,享年七十九歲。
譯者簡介
黃梅峰
法學碩士,曾任私立中國海專、崇佑企專法商及英文科目兼任講師。主要興趣為文學與藝術。曾譯《埃及古老故事》、《來自緬甸的聲音──翁山蘇姬》、《探索奇蹟》、《與奇人相遇》等書。
推薦序∕高銘和
登山史上最有名的一句話是:因為山在那裡。
說這句話的是英國有名的登山家喬治.馬洛禮。 一九二四年六月八日,他和厄文由西藏登聖母峰時,在爬到海拔約八五五○公尺的第二台階時,還被位於較低營地的另一位隊員觀望到,但之後就再也沒有他們的蹤跡了。 儘管後來有不少其他的登山隊伍由同一條路線攀登聖母峰,但從來就沒有發現過這兩位攀登聖母峰先驅的蛛絲馬跡。 一九五三年英國遠征隊的紐西蘭隊員希拉瑞和雪巴丹增,由尼泊爾登頂聖母峰成功,是人類第一次把足跡留在世界最高峰的歷史性壯舉。但他們所走的路線,並不是英國人早期想登聖母峰的西藏側路線,也就無法探究馬洛禮和厄文的消息。 一九六○年,中國由西藏登頂聖母峰,成為第一支由北側,也就是西藏登頂成功的隊伍,當年是藏族的貢布和漢族王富洲、屈銀華三人登頂,但因為是摸黑登頂沒有拍下照片為證,當時的國外登山界也就不太相信他們真的登上了頂峰。不過,在這次的行動中,隊員曾在六五○○公尺左右發現一具外國人的屍體,再於海拔七六○○及八三○○公尺兩處地點,發現一些英國隊遺留下來的登山裝備,如睡袋、麻繩等。這些發現曾引起西方特別是英國的注意,以為可以發現一些馬洛禮和厄文的消息,但最後也只是空興奮一場而沒有任何進一步的發展 到了一九七五年,中國第二次登頂成功,而且拍了照片和影片,西方國家才逐漸接受中國隊在一九六○年登頂的說詞。而一位隊員王洪保雖然只登到八六○○公尺,卻在八三○○公尺附近發現有外國人的屍體。這個消息傳開後,又再一次掀起西方國家想尋找馬洛禮和厄文的遺體的熱潮,可惜都無功而返。 一九九九年五月一日,由美國職業登山嚮導艾立克.希蒙生(Eric Simonson)率領的聖母峰遠征隊,在大約海拔八二五○公尺處發現了馬洛禮的屍體,衣領上還有Mallroy的字樣,這個重大發現轟動了全世界,因為它很可能會改寫人類登頂聖母峰的歷史性紀錄,把登頂聖母峰的年分從一九五三年向前推到一九二四年。當年馬洛禮和厄文最後被看到的地方是海拔八五五○公尺處,而馬洛禮的屍體卻在七十五年後的一九九九年,在低了約三百公尺的地方被發現,所以有人推斷他們已經登頂然後下到八二五○公尺處遇難;但也有可能沒登頂就下來而遇難。如果能找到他們攜帶的一台照相機,再應用現代高科技的方法把相機內底片的影像沖洗出來,也許就能判斷他們是否已經登頂。 楊.赫斯本所寫的這本《聖母峰史詩》,正是描述馬洛禮在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和一九二四這三年參加英國聖母峰遠征隊的前後經過,雖說楊.赫斯本並沒有親自參與攀登聖母峰活動,但是他曾在一九○四年前後率英軍進入西藏,對於喜馬拉雅山的地形和風土人情可以說是瞭若指掌,加上他又曾擔任當時英國聖母峰委員會的主席,所以由他來撰寫關於早期英國登聖母峰的歷史故事,是最合適不過了。 《聖母峰史詩》的內容非常豐富,特別是有關早期登山隊所需克服的人為或大自然的難關和阻力,做了很多詳細感人的描述,就算換成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那些情景對任何人也還算是非常艱難的挑戰。 讀完本書,除了對先民在探險事業上所做出的貢獻肅然起敬之外,對人類攀登聖母峰的歷史更有了全盤性的認知和了解,實在是一本值得一讀再讀的珍貴好書。
編按:一九九六年五月,高銘和先生率領九人「中華民國聖母峰遠征隊」參與攀登聖母峰盛會,並於五月十日在狂風中攀上心中夢想的山巔,成為台灣第一位從尼泊爾方向登頂成功的人。然而,當天下午的一場暴風雪奪走了來不及撤退的十二位世界級各國登山好手,造成了喜馬拉雅山登山史上最大的一場山難。其中高銘和先生順利生還,惟他全身多處凍傷,也失去了所有手指、腳趾、腳後跟及鼻子。不過,基於對山的眷戀,這位失去了手指與腳指的攀岩高手始終沒有愁容,修養後更帶著一年開刀十五次的大難後傷痕重返西藏高原,繼續「中國百岳」的拍攝工作。最近,他計畫在二○○八年整裝再度出發,與「台灣登山教育協會」組成台灣首屈一指的登山隊伍,重回令人敬畏的聖母峰。
導讀詹宏志山就在那兒
登山者當被問到為什麼要爬某座山時,常常給一個已經用濫了的詩意或者禪意的回答:「因為它就在那兒。」(Because it is there.)
從這句話我們也看出,「爬山登頂」本來沒有任何「實用的」價值,那是一種信仰激情或虛榮想像。文革時代插隊到雲南的小說家阿城有一次曾經對我說,在雲南深山裡,偶而有文明世界的外來客欲攀山登頂,山裡頭的村落居民對這樣瘋狂而無意義的行動感到不可思議,因而相信這些外來登山客有「神性」,不得不另眼相看…。
的確,爬上喜瑪拉雅山的西方人仰賴雪巴人(Sherpa)的幫忙,雪巴人千年來就住在喜瑪拉雅山山麓,卻從來沒想過要登頂;同樣的,第一位抵達北極極心的羅勃.派瑞(Robert Peary, 1856-1920)也仰賴愛斯基摩人的幫助,愛斯基摩人對他的奇怪目的地也感到不解,他們還曾認真勸他:「為什麼要去那兒?那裡什麼都沒有哇?」原始真誠的一句話,也有點「國王的新衣」的味道,偉大的目標常常有有某種「空洞性」,而「空洞性」有時候就是「神聖性」的另一種面貌。
但真正發明「因為山就在那兒」這句話的,是廿世紀初的一位天才登山家,他在1924年參加由愛德華.諾頓(Edward Felix Norton, 1884-1954)領軍的英國喜瑪拉雅山探險隊,在負責攻頂之後消失了蹤影,沒有再回到營區。這個悲劇不但在當時讓英國百姓黯然神傷,也使攀登喜瑪拉雅山的埃佛勒斯峰頂(如今為了尊重西藏人,都改稱珠穆朗瑪峰了)的行動停頓了三十年,他的名字叫做喬治.馬洛禮(George Mallory, 1886-1924)。
1924年6月8日中午時分,喜瑪拉雅山探險隊伍中的諾埃爾.歐岱爾(Noel Odell, 1890-1987)抬頭眺望,山上的雲層突然打開,他看見山頂岩壁上有黑點般的人影移動,他是這樣記錄的:
「12點50分,我發現第一塊埃佛勒斯峰確定的化石,正當我從狂喜中清醒過來,大氣突然晴朗清澈起來,整個埃佛勒斯峰頂稜線與峰頂頂尖都清楚可見。我的眼睛盯住了稜線下岩梯雪壁上的小黑影,小黑點正在移動。另一個小黑點也清楚了,它往上移動與第一個黑點會合於岩壁上。第一個黑點逼近岩梯巨石,很快地攀登上它,第二個黑點也接著做了同樣的事。但這個迷人的景觀很快就又消失了,雲層再一次包圍了它。」
歐岱爾是位地質學家,他這次的工作是準備氧氣筒,並且協助喬治.馬洛禮和另一位隊員安德魯.歐文(Andrew Irvine, 1902-1924)攻頂。馬洛禮和歐文前一天已經到達紮在雪壁上的六號營,高度是26800呎(8230公尺),離珠穆朗瑪峰頂只剩兩千多呎了,歐岱爾則留在五號營(25500呎,7775公尺)支援。前一個晚上,歐岱爾在五號營看見天氣良好,心裡覺得第二天應該是攻頂的好天氣。
12點50分他看見的移動黑影,應該是世人對負責攻頂的馬洛禮和歐文的最後目擊,事實上攻頂的行動顯然是擔擱了,按計畫他們應該在早上八點就到達12點50歐岱爾看到的位置。但上面的情況無人能知,在歐岱爾目擊雪壁上的黑點再度被雲霧遮掩之後,他們再也沒有音訊。
這也不是這支探險隊第一次攻頂,事實上這已經是第三次。第一次攻頂是由馬洛禮和另一位隊員,第二次攻頂由隊長諾頓和另一位隊員,第三次才由馬洛禮和歐文並肩行動。這也不是第一次英國組喜瑪拉雅山探險隊,這也是第三次。在另一位大探險家楊赫斯班德(Francis Younghusband, 1863-1942)的提倡與鼓吹之下,英國在1921年、1922年、1924年與組了三次企圖攀登喜瑪拉雅山的探險隊,以登山技巧和體能聞名的馬洛禮三次探險隊都參加了。
第一次探險行動主要目的是調查喜瑪拉雅山的地形狀況,他們攀登了數座七千多公尺的高山,並且踏勘了後來的北路登山路線。第二次探險隊的目標已經是直接攻頂了,他們嘗試使用瓶裝氧氣,也在惡劣的天候中攀登至山峰北面的岩壁上(大約是27000呎,8300公尺),最後的行動因為雨季來臨而中斷,當馬洛禮率隊友回程下山時,遇見不穩新雪造成的雪崩,七名雪巴挑伕因而喪生,使得馬洛禮返鄉後飽受批評。這是第三次探險隊成行時,馬洛禮志在必得的心理背景。
馬洛禮的失蹤對英國社會震撼極大,舉國上下幾乎是以失去「民族英雄」的心情來對待兩位消失的登山家。攀登喜瑪拉雅山的壯志也因而受了重挫,等到英國登山界再組探險隊,由約翰.韓特(John Hunt, 1910-1998)領軍,並由紐西蘭登山家艾德蒙.希拉瑞(Edmund Hillary, 1919- )和雪巴人嚮導天增.諾蓋(Tenzing Norgay, 1914-1986)正式由南路攻頂成功,那已經是1953年5月29日的事,距離歐岱爾最後看見雪壁上馬洛禮的黑點身影,已經快三十年了。
但世人忍不住還是要想,馬洛禮發生什麼事?驟變的氣候?還是用罄的氧氣帶來的意識不清?還是雪崩或失足?世人也忍不住更想知道,出事之前他們到底登頂了沒有?在雲開天清歐岱爾最後目擊他們時,他們已經越過了岩梯第一階(First Step,珠穆朗瑪峰北路的最後一面岩壁有階梯似的刻痕,第一階約在27890呎到28000呎,第二階在 28140呎到28300呎,第三階則在28510呎到28870呎,過了完這三階岩梯,再經一段緩坡就到峰頂),來到第二階,也就是說,他們距離峰頂只剩不到三百公尺了,他們極可能才是史上最先抵達第一高峰峰頂的人。
尋找馬洛禮和歐文遺體,當然也是世人關心的事。1999年,在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和其他組織的贊助下,一支由跨國登山家組成的搜查隊伍「馬洛禮、歐文調查探險隊」(Mallory and Irvine Research Expedition)登上北路進行搜索,彷彿天意,他們竟然很快地在8155公尺處找到了馬洛禮的遺體。由於嚴寒的氣候,馬洛禮的遺體與遺物都保存良好。他顯然是摔落山壁的,右腿已經斷了,手指還緊抓雪地石塊,想要阻止自己進一步摔下來,繩子也還綁在腰上。
探險隊最想找到遺物是馬洛禮隨身攜帶的柯達袖珍相機(Kodak Vestpocket),如果相機能夠找到,他生前是否登上峰頂就可以有答案。可惜上帝一向愛出謎語,搜索隊找到馬洛禮的人以及他大部分的遺物,相機卻已經不在了。
有一些間接證據,讓某些人和登山專家相信他們是登上過峰頂的。一個旁證來自馬洛禮的女兒,她說她父親隨身攜帶妻子的照片,但他說一旦登上峰頂,他會把妻子的照片留在喜瑪拉雅山頂上,搜索隊伍在他身上找不到這張照片。另一個證據來自於時間判斷,搜索隊發現馬洛禮的護目鏡放在口袋,表示極可能他最後行動時天色已昏暗;對照歐岱爾看見他們的時間,他應該是上了峰頂而且待了一段時間才下山,如果他們沒登頂,他們沒有理由擔擱到那麼晚才下山。但這些都是推測,沒有任何紮實的證據能夠告訴我們究竟發生什麼事…。
編輯前言詹宏志
.探險家的事業
探險家的事業並不是從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才開始的,至少,早在哥倫布向西航行一千多年前,中國的大探險家法顯(319-414)就已經完成了一項轟轟烈烈的壯舉,書上記載說:「法顯發長安,六年到中國(編按:指今日的中印度),停六年,還三年,達青州,凡所遊歷,減三十國。」法顯旅行中所克服的困難並不比後代探險家稍有遜色,我們看他留下的「度沙河」(穿越戈壁沙漠)記錄說:「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為標識耳。」這個記載,又與一千五百年後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穿越戈壁的記錄何其相似?從法顯,到玄奘,再到鄭和,探險旅行的大行動,本來中國人是不遑多讓的。
有意思的是,中國歷史上的探險旅行,多半是帶回知識與文化,改變了「自己」;但近代西方探險旅行卻是輸出了殖民和帝國,改變了「別人」。(中國歷史不能說沒有這樣的例子,也許班超的「武裝使節團」就是一路結盟一路打,霸權行徑近乎近代的帝國主義。)何以中西探險文化態度有此根本差異,應該是旅行史上一個有趣的題目。
哥倫布以降的近代探險旅行(所謂的「大發現」),是「強國」的事業,華人不與焉。使得一個對世界知識高速進步的時代,我們瞠乎其後;過去幾百年間,西方探險英雄行走八方,留下的「探險文獻」波瀾壯闊,我們徒然在這個「大行動」裡,成了靜態的「被觀看者」,無力起而觀看別人。又因為這「被觀看」的地位,讓我們在閱讀那些「發現者」的描述文章時,並不完全感到舒適(他們所說的蠻荒,有時就是我們的家鄉);現在,通過知識家的解構努力,我們終於知道使我們不舒適的其中一個解釋,就是薩依德(Edward W. Said)所說的「東方幻想」(Orientalism)。這可能是過去百年來,中文世界對「西方探險經典」譯介工作並不熱衷的原因吧?或者是因為透過異文化的眼睛,我們也看到頹唐的自己,情何以堪吧?
.編輯人的志業
這當然是一個巨大的損失,探險文化是西方文化的重大內容;不了解近兩百年的探險經典,就不容易體會西方文化中闖入、突破、征服的內在特質。而近兩百年的探險行動,也的確是人類活動中最精彩、最富戲劇性的一幕;當旅行被逼到極限時,許多人的能力、品性,都將以另種方式呈現,那個時候,我們也才知道,人的鄙下和高貴可以伸展到什麼地步。
西方的旅行文學也不只是穿破、征服這一條路線,另一個在異文化觀照下逐步認識自己的「旅行文學」傳統,也是使我們值得重新認識西方旅行文學的理由。也許可以從金雷克(Alexander W. Kinglake, 1809-1891)的(Eothen, 1844)開始起算,標示著一種謙卑觀看別人,悄悄了解自己的旅行文學的進展。這個傳統,一直也藏在某些品質獨特的旅行家身上,譬如流浪於阿拉伯沙漠,寫下不朽的(Arabia Deserta, 1888)的旅行家查爾士.道諦(Charles Doughty, 1843-1926),就是一位向沙漠民族學習的人。而當代的旅行探險家,更是深受這個傳統影響,「新的旅行家像是一個來去孤單的影子,對旅行地沒有重量,也不留下影響。大部分的旅行內容發生在內在,不發生在外部。現代旅行文學比起歷史上任何時刻都深刻而豐富,因為積累已厚,了解遂深,載諸文字也就漸漸脫離了獵奇采風,進入意蘊無窮之境。」這些話,我已經說過了。
現在,被觀看者的苦楚情勢已變,輪到我們要去觀看別人了。且慢,在我們出發之前,我們知道過去那些鑿空探險的人曾經想過什麼嗎?我們知道那些善於行走、善於反省的旅行家們說過什麼嗎?現在,是輪到我們閱讀、我們思考、我們書寫的時候。
在這樣的時候,是不是的工作已經成熟?是不是該有人把他讀了二十年的書整理出一條線索,就像前面的探險者為後來者畫地圖一樣?通過這個工作,一方面是知識,一方面是樂趣,讓我們都得以按圖索驥,安然穿越大漠?
這當然是填補過去中文出版空白的工作,它的前驅性格也勢必帶來爭議。好在前行的編輯者已為我做好心理建設,旅行家艾瑞克.紐比(Eric Newby, 1919- )在編(A Book of Traveller’s Tales, 1985)時,就轉引別人的話說:「別退卻,別解釋,把事做成,笑吠由他。」(Never retreat. Never explain. Get it done and let them howl.)
這千萬字的編輯工作又何其漫長,我們必須擁有在大海上漂流的決心、堅信和堅忍,才能有一天重見陸地。讓我們每天都持續工作,一如哥倫布的航海日記所記:「今天我們繼續航行,方向西南西。」
 我的第一本足球書
我的第一本足球書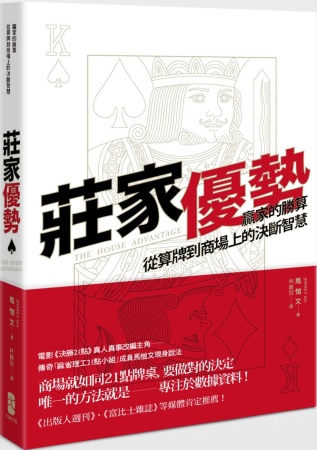 莊家優勢:贏家的勝算,從算牌到商場...
莊家優勢:贏家的勝算,從算牌到商場... 紐伯瑞文學獎精選套書3
紐伯瑞文學獎精選套書3 流水無歸程-三民叢刊122
流水無歸程-三民叢刊122 蘋果
蘋果 瞄準!軍事漫:CCC創作集17號
瞄準!軍事漫:CCC創作集17號 地擲球
地擲球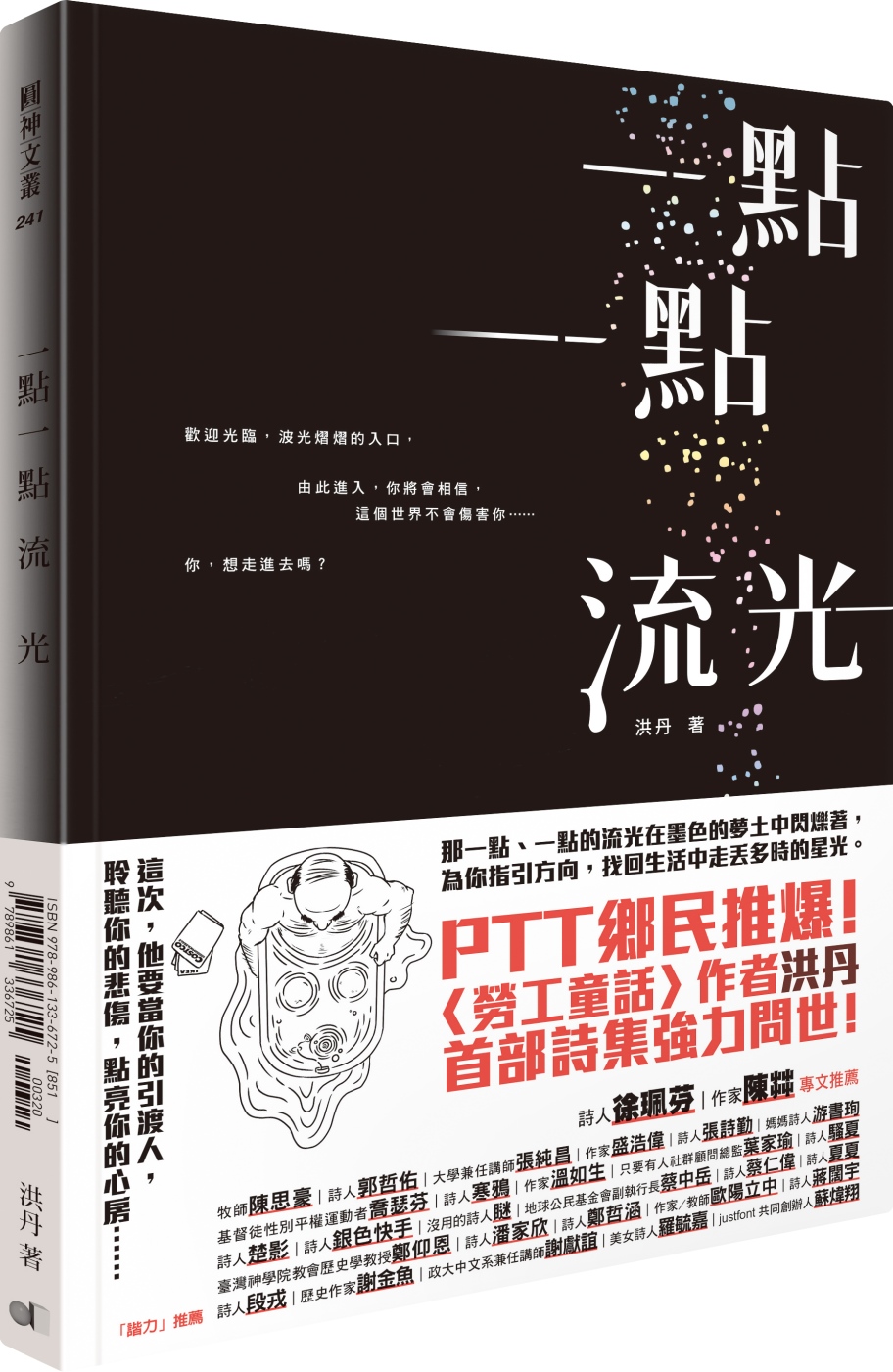 一點一點流光(中西兩翻雙書封設計)
一點一點流光(中西兩翻雙書封設計) 啃七四七飛機的男人
啃七四七飛機的男人 看穿假象、理智發聲,從問對問題開始...
看穿假象、理智發聲,從問對問題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