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族音影:書寫台灣.電影史 | 運動資訊第一站 - 2024年1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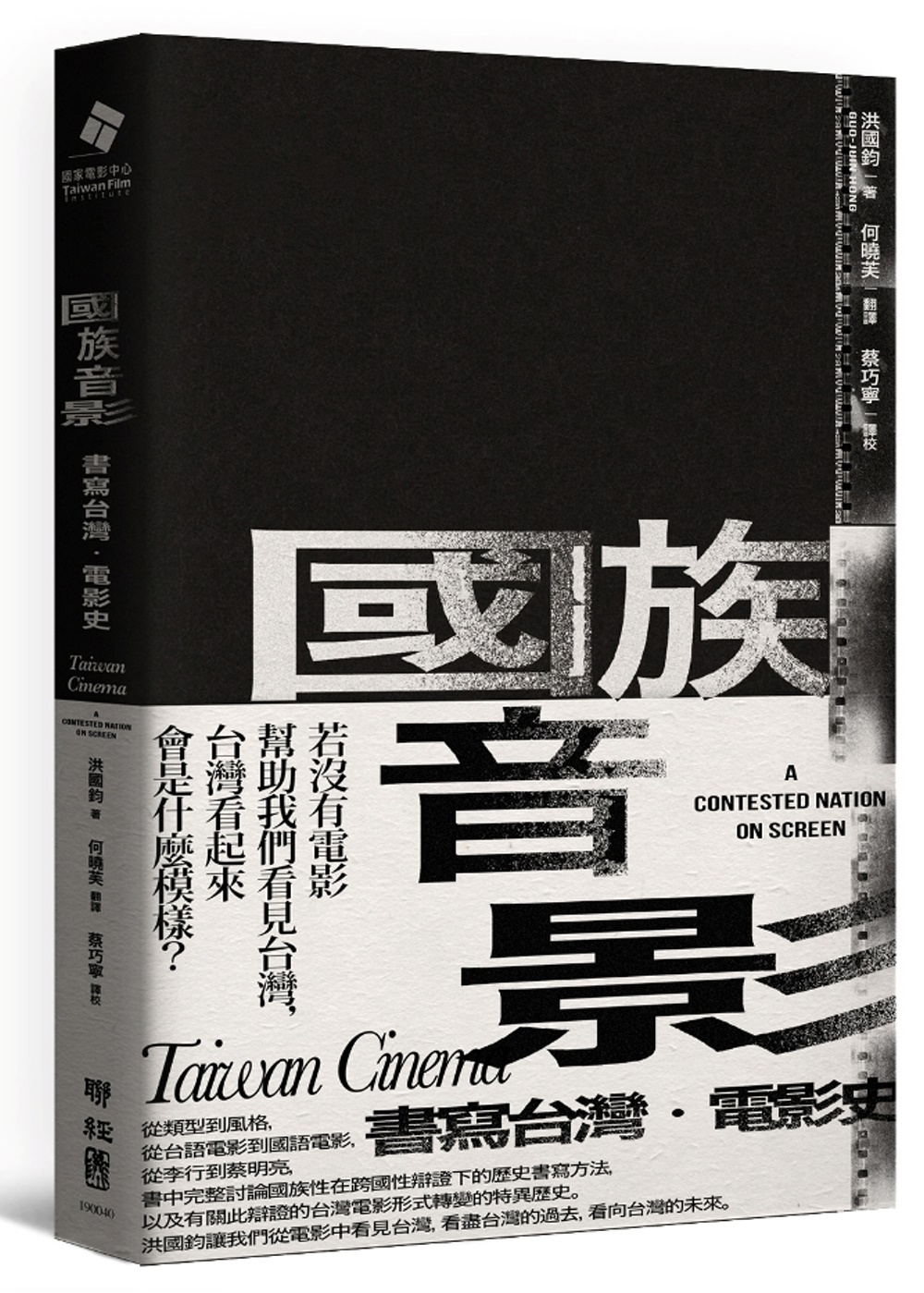
國族音影:書寫台灣.電影史
若沒有電影幫助我們看見台灣,台灣看起來會是什麼模樣?
從類型到風格,從台語電影到國語電影,從李行到蔡明亮,
洪國鈞讓我們從電影中看見台灣,看盡台灣的過去,看向台灣的未來。
台灣的國族電影是什麼?少了自己的電影,台灣看起來會是什麼模樣?
以「國族」的概念去架構或產出台灣電影史的故事是否恰當?
如果「國族」這概念曾經有效幫助美國以外的電影抵禦好萊塢的支配,
在當今跨國性主導一切的全球化時代,是否仍然有效?
洪國鈞的《國族音影:書寫台灣.電影史》深入梳理台灣紛亂歷史下國族與電影的關係,以細究「國族性」的框架。這座島嶼受到源於內部與外部的多重壓力,使得台灣成為生氣蓬勃又動盪不安的力場,這些壓力包括日本殖民遺緒、國民黨政府文化政策、各種本土主義運動與「中國」間的糾結,以及近幾年的全球化挑戰。以上壓力凸顯出台灣電影的歷史――包括形式的再現、映演和觀賞背景、類型的多元發展和風格的探索――正是台灣電影的「國族想像」持續更迭變動而造成的歷史,這樣的歷史特徵形塑了台灣電影,同時也受到台灣電影的挑戰。
洪國鈞堅持歷史的嚴謹與理論的彈性,將「國族」置於歷史、政治、文化脈絡,以及建構此概念的論述脈絡之中。他爬梳電影、文字紀錄、史籍檔案來回顧台灣電影歷史本身,並以歷史書寫的眼光重新檢視,仔細探究影像或其他文本如何作為論述和電影的問題意識,帶領我們穿越「國族」領域的討論。
《國族音影:書寫台灣.電影史》一書提出,電影在處理國族問題上的掙扎,是否反映出大眾對於國族的態度轉變?電影是否預期到這些改變而作為身先士卒的領頭羊?抑或電影中的處理,其實牴觸一般大眾的想法,顯示出構築台灣身分的方式並不止一種?改變的發生是否會帶來轉折,若有,又是怎麼樣的轉折?當多重的殖民歷史、國際政治與台灣電影的歷史緊密交織,我們如何在國族性受到政治性干涉與維持的同時,將其作為批判框架,對跨國性影響下的台灣「國族」電影歷史提出更有效的省思?本書將討論國族性在跨國性辯證下的歷史書寫方法,以及有關此辯證的台灣電影形式轉變的特異歷史。
各界推薦
王德威、張小虹、李道明、史書美、林文淇、林松輝、邱貴芬、柯裕棻、孫松榮、郭力昕、陳斌全、陳儒修 聯合推薦
電影如何呈現民族風采、在地特色?國家如何形塑電影風格、文化工業?《國族音影》聚焦臺灣,縱論百年臺灣電影工業與國家體制的互動與分歧,表現與發明。洪國鈞教授史識寬闊,論述翔實,見解深刻。從殖民到後殖民,從健康寫實到後現代解構,從李行到蔡明亮,臺灣歷史虛實流變,如電如影。本書是任何關心臺灣與世界電影、與國家民族主義及現代性追求不容錯過的佳作。──王德威(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系暨比較文學系講座教授)
洪國鈞將台灣電影研究帶入了新的紀元,不僅讓「國族」成為「音影共同體」的流變生成,更讓「後國族」的美學政治思考成為可能。《國族音影》透過對(後)殖民歷史的差異詮釋,讓你/妳看見不一樣的台灣而驚異讚嘆。──張小虹(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特聘教授)
國鈞的書出現在21世紀10年代,提醒西方電影學術界重新思考與認識台灣電影史,尤其是關於西方人極少知道的日治時期及戰後民國40至60年代的台灣(通俗)電影。國鈞試圖「挑戰」西方電影史的「典範」,也為「失聲」的台灣電影(史)發聲,是所有研究台灣電影與台灣歷史的學生與學者都應該閱讀的一本有價值的學術書籍。──李道明(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客座教授)
作者簡介
洪國鈞(Guo-Juin Hong)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修辭學和電影學博士,從2004年起開始發表一系列有關1930年代上海電影、紀錄片和同志運動等主題的文章。2009年以〈1930年代上海的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 in 1930s Shanghai)榮獲電影與媒體研究學會頒發的Katherine Kovacs論文獎。現為杜克大學華語文化研究副教授,開設課程包括華語電影、中國文學和文化、電影理論和電影史學、劇情片、紀錄片和視聽文化。
譯校者簡介
蔡巧寧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畢業,自由譯者,熱衷於電影、藝術、烹飪、旅行,現居杜拜。
譯者簡介
何曉芙
國立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文學組碩士,曾為自由譯者,現從事電影相關工作,翻譯仍是最美好的興趣與調劑。
推薦序 更深入理解台灣電影的途徑/國家電影中心執行長 陳斌全
謝辭
導論 台灣電影與缺席的歷史學
第一部 類型
第一章 殖民與後殖民的考掘:戰前台灣,以及「國家」出現前的紛雜文本
第二章 類型與國族的糾葛:台語電影二十年,1949~1970
第三章 行者影跡:健康寫實主義、文藝政策與李行,1964~1980
過場 侯孝賢之前的侯孝賢:過渡時期的電影美學,1980~1982
第二部 風格
第四章 回首來時路:台灣新電影的興衰,1982~1986
第五章 前往島嶼的單程票:王童作品中的回顧式電影敘事
第六章 無所/不在:蔡明亮台北三部曲的後殖民城市
後記 後國族時代的電影
平裝版後記 未曾消散的歷史:何謂國族?
推薦序
更深入理解台灣電影的途徑
陳斌全(國家電影中心執行長)
在今日,台灣電影產業已由《海角七號》(2008)等影片開啟的所謂「後新電影」時期,進入類型掛帥、跨國製作的階段;但是在區域化與全球化的角力下,表現在電影題材與類型間的差異卻愈見分明。鑑古知今,過往台灣電影曾經走過的每個重要階段:由台語片到健康寫實國語電影,乃至於世界電影範疇裡重要的「台灣新電影」,尤其需要歷史化的脈絡論述。洪國鈞教授的大作《國族音影:書寫台灣.電影史》於是呈現台灣電影從殖民到後殖民、再到全球化時代,形式與內容持續與國族歷史框架抗衡的步履;其中一個可貴的論點清楚闡明,1980年以特定導演為核心的「台灣新電影」的出現,即便當時的本土電影工業體質並不強健,因而讓新電影看似是在外片壓力、政府文藝政策,和商業需求之間所開出的奇花異果,卻亦非憑空而來。
洪教授於書中指出,台灣電影起始於「沒有電影的電影史,沒有國族的國族電影」。在最早的日治時期,僅以新聞片和紀錄片為重心;戰後初期國民黨政府主導的電影製作,則以國族意識教化作為放映目的之媒體性質展現,卻促使民間產製的台灣電影在萌芽之初便發展出一種「在地混雜性」,標示出獨特的台灣電影景觀。這段隱然可被探知的「國族」與「電影」的相互建構、競逐過程,在洪教授細密地透過分析敘事和敘述手法、反思類型形式與視覺呈現之下,逐章顯影,這其實也正呼應影像文本本身可被視為歷史書寫,甚至是超越歷史書寫的體現。
台灣新電影的出現,即是在後殖民、分裂的官方「國族」歷史與家庭敘事主題陰影下,其美學與風格上的跨越。洪教授指出新電影的出現,尤其展現歷史轉變的抗衡與特殊抵抗形式,台灣新電影的電影策略再現與國族主義相抗衡的現代性,這正是健康寫實主義在美學與政治之間陷入遲滯,由同樣寫實主義取向的新電影繼而代之,重新將美學政治化,成為一種再興的國族歷史書寫。就此看來,台灣的國族音影的整體樣貌已然呼之欲出。
本書的英文版於2011年問世,七年之後,國家電影中心策辦的第十一屆(2018)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放映由國影中心自主修復的陳耀圻導演作品《上山》(1966)。從影片的美學呈現來看,相較於過去一直被認定,標誌出台灣紀錄片現代意義的陳耀圻導演另一部紀錄片作品《劉必稼》,《上山》反而更貼近1960年代國際紀錄片潮流的手法。影展的另一焦點,牟敦芾導演於1960年代末期的作品《不敢跟你講》與《跑道終點》,其內容與形式亦令人驚豔。由前述幾部重映的作品來看,台灣電影工作者在國族和現代性之間的折衝探討,以及為了尋求去殖民而將他者本土化的嘗試,在1980年代台灣新電影之前便已出現,正好印證洪教授書中的主要觀點。
在此作為補充的是,紀錄片作為另一種寫實主義的形式展現,亦不失作為健康寫實主義、新電影其美學過渡期間的參照與辯證。如今洪教授這本具有高度學術價值的《國族音影:書寫台灣.電影史》中文版面世,個人相信必定能提供有志於台灣電影史的研究者,以及喜愛電影的普羅大眾,更深入理解台灣電影的另一途徑。
導論(節錄)
國族電影的爭議
1993年我初次離開台灣,抵達美國不滿一個月,便選修了人生第一門電影史課程。那堂課指定的是《電影百年發展史》(Film History: An Introduction)這本廣受學界採用的電影教科書,但書中對台灣電影的介紹讓我大為震驚。作者克莉絲汀.湯普森(Kristin Thompson)和大衛.鮑威爾(David Bordwell)像是偶然獲得了人類學的新發現,欣喜地驚嘆道:
1982年的台灣,在電影製作上毫無創新可言,當時的作品聲名狼藉,若非迂腐的政治宣傳工具,就是未臻成熟的低成本娛樂。然而,到了1986年,台灣已成為國際電影文化中最令人振奮的區域之一。
這種視1982年以前的台灣電影為「政治宣傳」──政治支配媒體,或是「未臻成熟」──庸俗娛樂凌駕藝術,因而不屑一顧的看法,即便於二十年多後的今天看來,仍不免使讀到此書的台灣電影研究者十分詫異。
對湯普森和鮑威爾而言,在新電影時期之前,台灣「不太可能」已發展出「創新」的電影製作;然而,到了1986年,台灣已成為全球藝術電影的核心重鎮,足以令人「振奮」。關於1982年至1986年之間發生的種種轉變,也許大家都很清楚,但疑問依然存在。1982年以前的情況究竟如何?在闖入國際視野之前,台灣電影到底是怎樣的面貌?當時製作了哪些類型的電影?製作目的又是什麼?難道處於威權政體統治之下,再加上電影工業基礎貧乏、國際壓力頻頻來襲,所有電影都必然毫無價值嗎?簡而言之,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台灣電影在1982年以前的缺席現象?
被納入全球視野之前,台灣電影究竟是何樣貌?湯普森和鮑威爾使用的關鍵字提供了一些線索。首先,「創新」一詞已預設新電影別開生面,也就是「跟過去的電影有所不同」。「創新」也樂觀地暗示,新電影為往後的發展鋪成了道路,想當然耳,未來的模樣也將與此時有所不同。換句話說,「創新」不只存在於某一個時點,而是一段持續的時間,包含「呈現時間」(represented time)──從過去直到創新改變發生之際──以及「投射時間」(projected time)──由創新引領邁向未來的一段時期。因此,台灣電影的歷史其實是透過「雙重中介」(double mediation)來書寫的:一方面,在歷史學者下筆之前,台灣電影並沒有歷史;而另一方面,學者筆下的歷史,卻又奠基於大量缺失的「前」史之上。台灣電影是在尚未產生自己的歷史論述的缺憾之下被以西方觀點寫進全球電影史之中。《電影百年發展史》中對1982年前台灣電影那種不符合歷史真實的看法,數十年來於多次再版中持續留存,這個現象確實讓我們無法忽視。
在湯普森和鮑威爾的看法之外,透過其他版本的「世界電影史」書寫,我們還可以看出華語電影研究當中有另一項截然不同的挑戰,同樣導致1982年前的台灣電影缺乏能見度。在另一個版本的論述中,台灣竟是仰賴「中國第五代導演」才得以進入全球電影史。在《電影的世界史》(A World History of Film)一書中,作者羅伯特.斯克拉(Robert Sklar)特別以侯孝賢來介紹台灣電影。侯孝賢是八○年代台灣新電影的核心人物,在往後的電影發展中也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斯克拉卻只著重在侯孝賢曾經加入中國導演張藝謀《大紅燈籠高高掛》的製作團隊這件事──斯克拉是這麼說的:「這也許會讓所有認識亞洲電影的閱聽眾感到吃驚。」但是,台灣電影之所以值得一提,本該基於電影創作者自身對於世界電影的貢獻,而非仰賴其與中國電影的關聯。儘管侯孝賢遠比張藝謀更早就開始擔任導演,但由於斯克拉將台灣電影視為中國電影的「子類型」,因此侯在斯克拉的電影史中的定位竟然是張藝謀的附屬,這才是真正讓人驚訝之處。
斯克拉建構的全球電影史觀聚焦於特定的區域上,這點是他與湯普森和鮑威爾的差別。然而,全球各地華語電影各自盤根錯節的歷史,與同樣錯綜複雜的世界電影歷史同時發生、相互碰撞,從動盪的二十世紀到今日,分歧不均的轉變綿延交錯。上述兩種歷史書寫都採取了分層結構(stratified structure):以空間為基底來組織歷史,並根據「核心─周邊」的邏輯來形塑概念,最重要的是執守於可見性(visibility)與缺席(absence)之間的辯證關係。在此概念下,中國電影占據了核心位置,台灣電影僅為其周邊。本書則採取不同的書寫策略,首先是用時間量尺來深化歷史厚度,並在空間上將台灣分立出來,根據台灣自身的價值賦予其歷史意義。
本書所探討的核心問題很簡單,也不斷被探問過:台灣的國族電影是什麼?以「國族」的概念去架構或產出台灣電影史的故事是否恰當?如果「國族」這概念曾經有效幫助美國以外的電影抵禦好萊塢的支配,在當今跨國性主導一切的全球化時代,是否仍然有效?簡言之,究竟什麼是國族電影?
安德魯.希格森(Andrew Higson)在〈國族電影概念〉中嘗試全面檢視「國族電影」一詞,他用英國電影來論證,列舉四種可以用來定義國族電影的論述框架:經濟、映演或消費、電影文本、電影批評。這些辭彙的類別特徵顯露出某種歐洲中心主義,而忽略了區域特異性。正如希格森後來坦言,這篇文章屬於「假定能適用於所有國家的泛用國族電影理論」。然而,為了將國族電影「重新概念化」,史蒂芬.庫洛夫斯(Stephen Crofts)以更複雜的思維將希格森的模式推及到非西方電影,納入多元的全球電影脈絡和各種電影產製模式,例如歐洲藝術電影、第三電影、極權電影、地區/族群電影,還有「刻意忽略好萊塢」的電影。國族電影因此成為各種辯證組合,依照希格森後來的理論歸類,即為「國族主義與跨國主義」和「文化多樣性與國族特異性」之間的辯證。這樣的拉鋸使得國族性跳脫以往既定的國族電影框架。「透過電影想像出來的浮動社群,比起國族性,反而更具本土性或是跨國性。」國族電影的概念最終被視為不穩定、可變動,並具備歷史性。我們在本書可以看到,「歷史」本身一直受到攻擊,而角力拉鋸總是由「國家」引發的。
本書深入梳理台灣紛亂歷史下國族與電影的關係,以細究「國族性」的框架。這座島嶼受到源於內部與外部的多重壓力,使得台灣成為生氣蓬勃又動盪不安的力場,這些壓力包括日本殖民遺緒、國民黨政府文化政策、各種本土主義運動與「中國」間的糾結,以及近幾年的全球化挑戰。綜觀以上壓力,我凸顯出台灣電影的歷史──包括形式的再現、映演和觀賞背景、類型的多元發展和風格的探索──正是台灣電影的「國族想像」持續更迭變動而造成的歷史,這樣的歷史特徵形塑了台灣電影,同時也受到台灣電影的挑戰。
台灣電影自始便具有跨國性,本書第一章討論殖民時期的部分將有所闡述。若想理解台灣電影,最好的方法是將「國家」視為內外抗衡的樞紐,並將國族性與跨國性看作一組辯證關係。我堅持台灣的定位不應只取決其與中國的關係,而應與東亞地區整體連結,甚至要放在全球脈絡下研究。如此一來,才能避免僅將國族性看作簡化或過時的概念,導致忽視其至今仍持續存在且處處可見的意識型態功能。否則,我們將可能過度強調跨國性就是跨越既有疆界,誤以為能超脫其間的差異,實際上卻忽視了各實體的特定歷史與條件。
在此我要提出兩組息息相關的問題意識,它們有助於分析這種緊張關係。首先,若以跨國或甚至全球化電影之名,視國族電影為過時的類別而將之屏棄,便無法解釋這個現象:對「非好萊塢電影」來說,國族性至今如何又為何仍是常見的理論架構,用以構築批判論述、操作政治修辭。其次,儘管國族性備受爭議,至今卻仍具影響力,那麼「國族」這個概念本身的歷史沿革又是什麼?而這頗具爭議的辭彙又是如何在論述和電影中呈現?達德利.安德魯(Dudley Andrew)主張國族電影的「海洋綜覽」(oceanic view),特別針對各式各樣需以國族性角度檢視的新浪潮。安德魯將之比喻為「電影海洋中的島嶼」,鼓勵詳加分析這些新電影,認為這些新電影不僅在分歧的全球脈絡中擔綱要角,同時也藉由電影來回應全球脈絡。國族電影絕非故步自封、一味屏除跨國性的領域;跨國性其實正是國族性的先決條件。為了研究跨國華語電影的構成,我認為首先必須審視「國族」在歷史、論述、電影中如何被形塑而成。
問題在於台灣的歷史特異性。陳光興稱「全球本土主義」(global nativism)為台灣電影的特色,採取這個出發點雖有助益,卻使得複雜的歷史變得平板。「全球」和「本土主義」都是至關重要的重點辭彙,框架出今日我們理解台灣電影的一種方式,理當加以著墨。我們必須認知,台灣歷史特有的「密集殖民性」形塑了本土主義的生成,並影響本土與全球競爭抗衡的形式。此外,史書美特意措辭聳動地將台灣定位為「不重要」,藉此凸顯其重要性。許多台灣電影工作者過去二十年的傲人成績,卻在全球電影流通之下,諷刺地抹除了台灣具有歷史特異性這個面向。尤其是當個別電影工作者被標誌為「國族」代表時──電影作者替代了國族──國族論述滿足了跨國主義的胃口,將「國族電影」轉化成導演、電影、獎項等各種得以獨立辨識的物品,注入全球消費流通。
第一章 殖民與後殖民的考掘──戰前台灣,以及「國家」出現前的紛雜文本 1945年,大分裂下的台灣 1945年8月6日、9日,原子彈落在廣島和長崎。一週之後(8月15日),裕仁天皇透過廣播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歷經五十五年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即將回歸中國。四十多年後的1989年,知名台灣導演侯孝賢以天皇當年的廣播錄音作為電影《悲情城市》的片頭。天皇的聲音單調而平板,聽來頗為含糊,銀幕上則一片漆黑。接著,家族神龕終於點起一根蠟燭,燭光搖曳,深刻地提示了這是電影再現的台灣歷史。在劇情敘事中,這場戲發生於停電之際;可想而知,日本天皇的廣播演說一定是在別處放送,此時以畫外音與渾然不知的角色們共存。 影像語言(cinematic apparatus)同步呈現了這兩起事件,雖然不太和諧,卻是電影再現歷史的方法之一。一方面是官方廣播宣布台灣殖民告終,另一方面是殖民時代下的庶民日常,電影縫合這兩個特別的場景,展現台灣電影中後殖民歷史書寫的一個重要面向。在光明與黑暗之間,透過影像的重建,似乎成為台灣紛亂歷史最適合的背景。同時,在沉默與言語之間,《悲情城市》交由聾啞主角來述說歷史,藉由多重的語言環境,輔以旁白與字卡,以各自分歧又相互交織的故事線豐富劇情敘事。《悲情城市》揭露台灣與殖民遺緒深深糾葛的黑暗歷史,更藉由無法發聲的角色發言,用漸漸加強的本土對位聲音,來對抗官員的權威語言,呈現了電影對台灣歷史的想像與再現。電影正是台灣歷史書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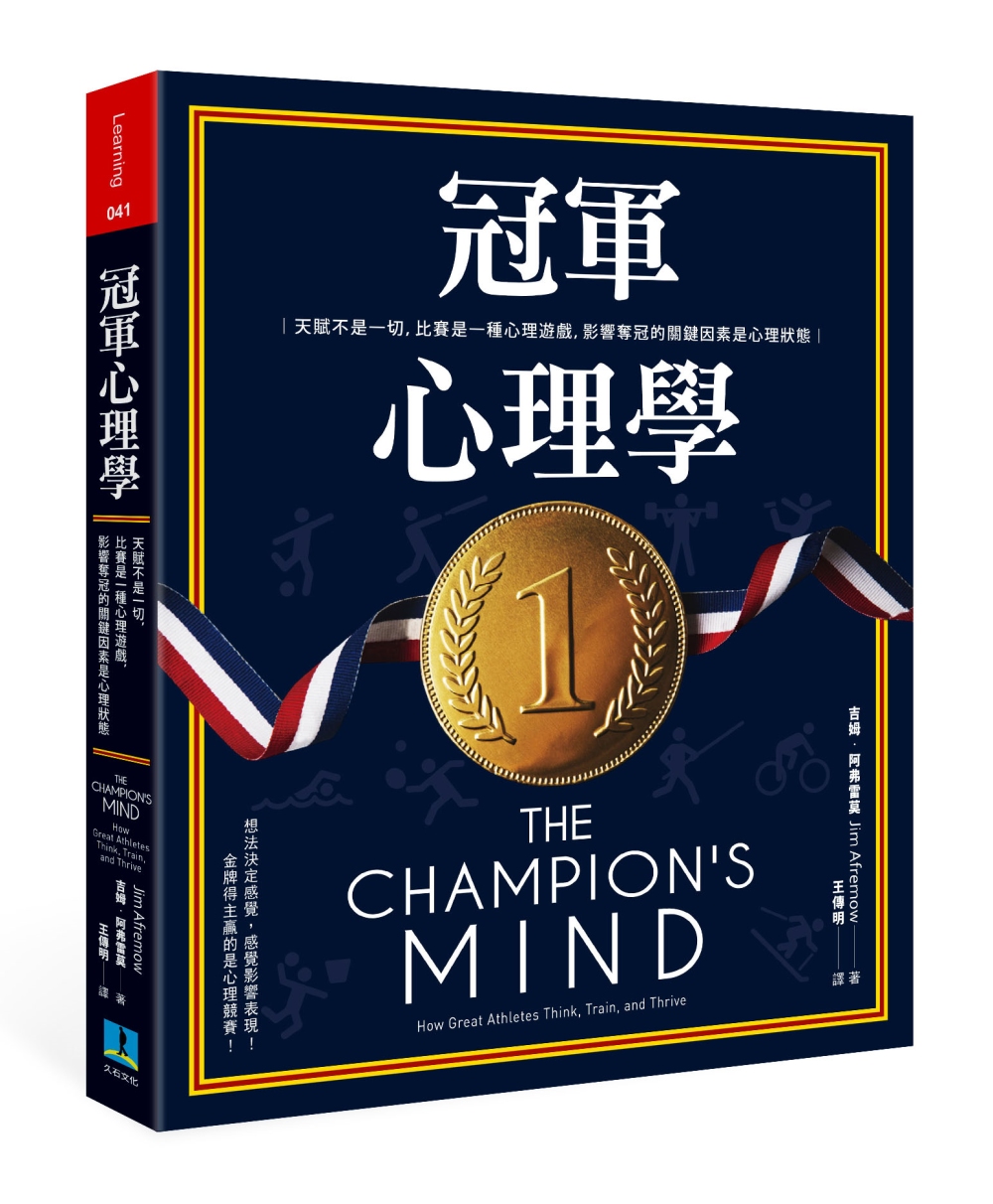 冠軍心理學:天賦不是一切,比賽是一...
冠軍心理學:天賦不是一切,比賽是一... 超熱血!動物瘋奧運:如果動物們去參...
超熱血!動物瘋奧運:如果動物們去參... 永不放棄的跑者魂:真男人的奧運馬拉松之路
永不放棄的跑者魂:真男人的奧運馬拉松之路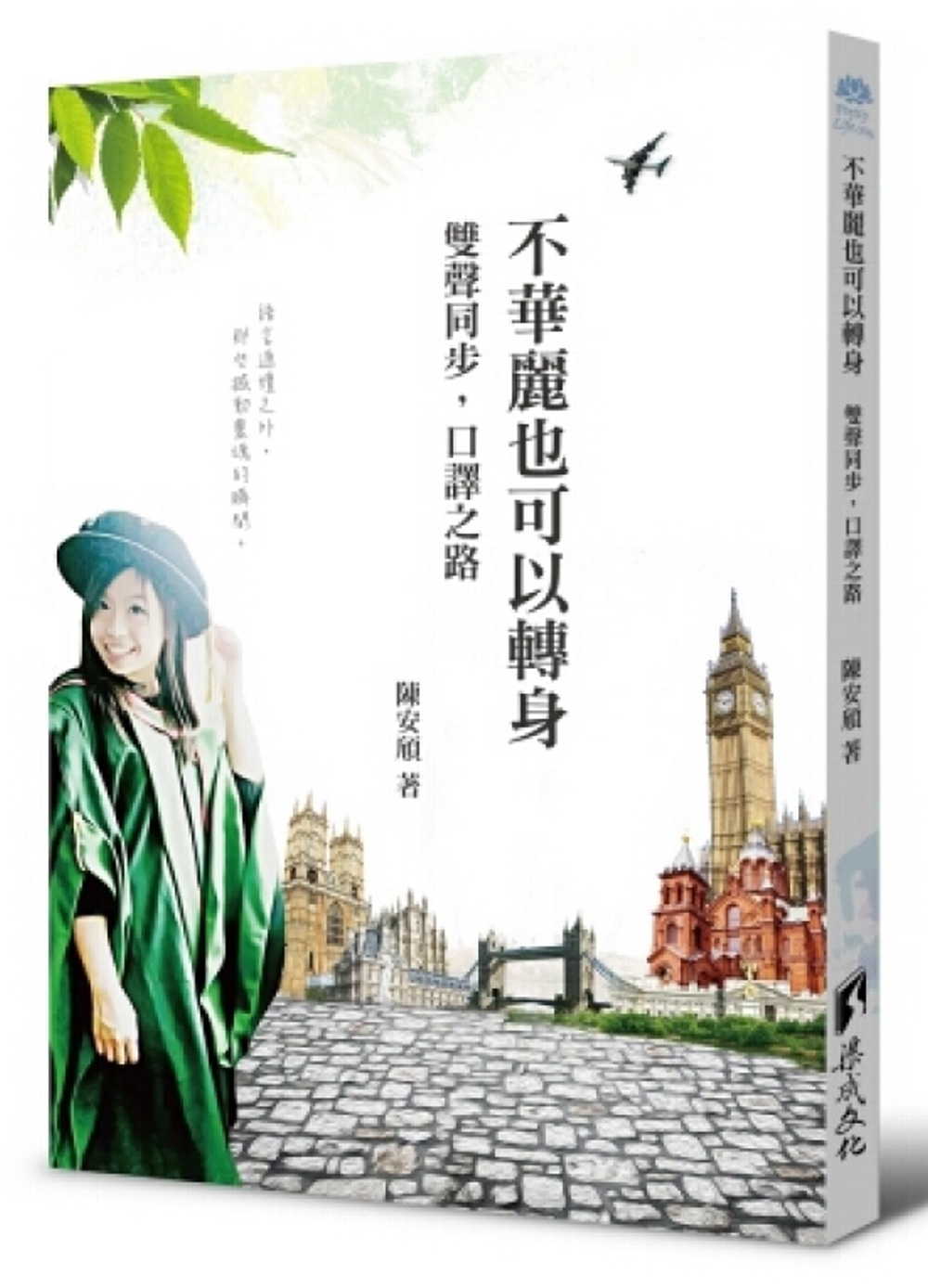 不華麗也可以轉身:雙聲同步,口譯之路
不華麗也可以轉身:雙聲同步,口譯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