蛆樂園 | 運動資訊第一站 - 2024年11月

蛆樂園
首部以艋舺流浪漢為題材的推理小說!
游離於偵探與恐怖之間,深掘出社會邊緣的寫實,
愈深入,愈是迷亂,反而愈接近真相……
〈蛆樂園〉
我們存在的世界,美麗與醜陋,總是相伴而生。
繁華的臺北城是個大斗,斗上坐滿光鮮亮麗的臺北人,爬不上去的,在斗壁上掙扎,上上下下,上了又下,或者,下了又上;而遊走於社會邊緣的流浪漢,不但爬不上去,還一路滾到窄窄的斗管底。
然而,斗管底的世界,便是那座新艋舺樂園。斑駁卻艷麗異常的新樂園。
〈流浪者之歌〉
三個人物,三道人生軌跡,卻同樣流連、沉醉於社會的一角。
省吃儉用、滿心想快快見到女兒的單親媽媽,與嗜菸酒如命的半盲流浪漢,以及只想著滿足口腹之慾的男子,背負著各自的苦痛,為灰暗卻透著微光的人生,織出一曲〈流浪者之歌〉……
蘇飛雅以小說之筆,搜集流浪者的悲苦與血淚,擴寫他們在命運懸崖邊掙扎求生存的驚險實況,彷若一本臺灣街頭景況的人物速寫。
名人推薦
吳鈞堯/幼獅文藝主編、作家
林菁菁/健行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林金郎/白象文化經理、文藝評論家
保溫冰/新銳影評人
張啟疆/小說家、文學圓夢班主持人
張經宏/小說家
許榮哲/四也出版總編輯、小說家
郭漢辰/作家
蔡淇華/臺中市立惠文高中圖書館主任、作家
鍾文音/作家
謝文賢/小說家
浮沉黑暗中,那些蠕動的身影裡,可以見到的不僅僅是蛆,而是飽含各種慾望的真實人生。藉由文學的創作及書寫,讓微光穿透進去,讓人們感受到一絲絲溫暖。──郭漢辰
作者簡介
蘇飛雅
臺北出生,艋舺求學,板橋長大。住過鶯歌、永和、萬華、板橋、淡水。如今回想起來,一切的一切,都與母親讓我越區就學有關,我的整個小學時期,都在越區就學,沒有公車、客運、火車、計程車,我簡直沒法上學,那麼長的通車時光,等車的苦、乘車的擠、到站時被人群推迫而下的輕鬆……就這樣形塑了我的童年。不苦不擠的時候,上車到下車的一小段時光,彷彿跌落黑洞,旋轉、翻滾、發呆,默想、驚喊、沉睡。
等我從白洞探出頭時,世界已經不一樣了。
一次又一次,我是張曉惠,也是蘇飛雅。
推薦序
躁急的文字熊抱
張起疆
混亂而躁狂—我對蘇飛雅的小說印象。
很多年前,我對她說:「妳有一種癖習:在麻辣鍋裡添麻加辣。」
我嗅到,某種成長過程凝成生命印記,進而形塑了她對現實的「關懷」方式:羶腥、腐臭、困窮、躁動、茫亂。
一種,不堪且令人不安的庶民生活,社會底層浮世繪。
如果沒記錯,《蛆樂園》應是蘇飛雅筆耕多年的第一本結集。
超過十年了,從我第一次看她的作品到現在。她的發軔期遠在何時?我就不知了。十年磨一劍,衝撞跌宕,別具風情;試圖扣緊議題(如八八風災),也曾掀起文壇話題。這段奮戰過程,即使稱不上轟轟烈烈,作者本人想必銘刻在心。
這些年的蘇飛雅,堪稱「參賽游牧族」的一員大將。她來圓夢班上課那幾年,平均每年寫出約十篇萬言小說,看得我雜花生樹,眼睛脫窗,愈罵愈兇。有些小說稿,一改再修,像長出翅膀,飛繞在一手讀者我、評審委員和她的電腦檔案間。
十篇作品都是佳作?當然不可能!中心打者十次揮擊約有七次摃龜,天才演說家也做不到字字珠璣。十之一、二榮獲讚賞……哦不!我要說,十篇小說都得不到肯定或好評,怎麼辦?也,值得了。
寫。努力寫。抒發心志而寫,尋幽探微而寫,實現自我而寫,止痛療傷而寫,文火慢熱地寫,大火快炒地寫……或者,只是為得獎而寫,都好。
蘇飛雅屬於「快炒派」:下筆速度快,小說節奏也快;但故事的核心,不見熱情熱血,反而透著既餿且涼的人性冷嘲。
她的行文,屬於快板敘事,小說感十足:誇飾、怪誕、衝突不斷,以及,令人不忍卒睹的細節摹寫。
例如,描寫身上沾糞、傷口生蛆的遊民:
有些實習生尖叫起來,沒命似地躲進簾幕後,警察直接把那乳白色傷口揭給值班醫師,醫師也愣住,然後才慢慢湊過來,看清了那乳白色蠕蠕鑽動的傷口原來不是傷口,是一個滿滿的蛆窩,嚇得倒退三步,拿責備的眼神和警察對望,最後才喊來護士長,要她們把他拖進去。
這樣的「非人類」,還有一道小小的、性的「瞄」寫:
他不但是個人,還是個姣好的男人,他有陰莖,也有腿毛,和胸毛,有些護士退了出來,遠遠看著,竊竊說些讓人臉紅的話,方才的喧嚷停了下來,她們讓他自己著衣,自己走到候診椅。
諸如此般的文字表現,會讓你在閱讀時萌生一種沾黏感,好像摸黑走進髒腥廁所,遍地屎尿、痰血、蛆蟲、檳榔汁,揮之不去的惡臭在口鼻眼耳盤旋。小心!撲面而來的文字熊抱、意象勒頸,帶給你無從迴避的感官撼動。
這本《蛆樂園》,合兩中篇為一長篇,兩則故事各自獨立,卻有著極為相似的「底層描寫」:遊民或半遊民(舉牌工)的生活狀態,或者說,無家的悲悽恓惶。
〈蛆樂園〉中的艋舺國遊民,自不待言。阿強、拉皮珍、喇牙、炮妹、嘴瀾琴……等人,都有一段不堪聞問的過往。小說梗雖然建立在「死了一個遊民之後」的推理遊戲,一路鋪展的蛛絲馬跡,卻非關案情,而是傷心人的傷心事。
〈流浪者之歌〉更是將「家」的扭曲、分裂與潰散,呈現得生動淋漓。
例如,「女版史瑞克」李敬雅是在隔代且單親的家庭長大,父親再婚後,連父愛也失去了。
媽媽抱著弟弟關在一個房間,爸爸關在一個房間,她關在一個房間,三人各過各的,互不相讓也懶得搭理,他們都學會了溫柔地僵持、平靜地折磨彼此……
「口袋有破洞」的許聖凱的父母健在,原是一個表面和諧的家庭,卻在無意間撞見父親偷腥,戮破了幸福的假面。而他也變得消極頹唐,賺八百吃一千,滿腦子十六盎司肋眼牛排。
至於「老是做夢」的老孟,泰雅族的媽媽難產,河南籍的生父早死,而由待他苛薄的養父帶大。他生命中的重大災禍,車禍、在大陸掉皮夾回不了臺灣,都得不到養父的急難救助。
三名舉牌工,三個或者破碎或者冰冷的家,敷衍出有家歸不得的心靈流浪。難得「回家」一趟,李敬雅被擋在門外,老孟吃了頓冰冷晚餐,而不得不「苦笑著,輕輕帶上門,靜靜地走」。
和艋舺國國民依偎取暖、自成一家相比,舉牌工的故事,更顯觸目驚心,貼近我們的日常。即使是具有修補性質的戀情愛焰,阿強、阿瑛的擦槍走火,狂熱而甜蜜;李敬雅和許聖凱的配對……
她今年三十五,許聖凱才二十九,她身高一七三,許聖凱大概才一六八,怎麼說都很不搭嘎,但這點驚喜……夾雜害羞又略帶無聊幼稚的調酒般的怪異情緒,竟讓她感到一股酸酸甜甜的浪漫。一時間捨不得放,可是眼前確確實實是站著個小弟弟。
仔細看那一大一小靠著行走的淡影,有點像是頭大獸領著個小獸……
像一則滑稽的動畫。
或許,我該如此解讀蘇飛雅的首航:她的出發,猶似回歸。既是書寫「底層生活」,更是直探「底層生命」—家,不就是每個人的生命地基?
這個或許不經意的發軔點,一定和她的童年生活、身世背景有關。那是結?節?癤?有幸與這位創作者結緣十餘載的我,不願剖挖她的內心、肢解她的痛點,只想輕輕說聲:柔些,淡些,對比些。
苦笑或微笑,輕輕打開門,慢慢走進去……
死了一個遊民之後 一 那身軀攤在艋舺公園的草地上,好像許多年的辛勞終於卸下。 周圍很多垃圾,飲料罐、塑膠袋、檳榔渣、空酒瓶,還有沖天炮殘骸、燒爛一角的煙火盒子,狂歡之後難堪的荒蕪與雜亂,通通攤在微亮而骯髒的天空下。 可是那身軀很享受。 喇牙觀察了好久,終於走過來察看,一看清那鬍渣、那眉眼鼻後,露出驚訝的表情,轉身看著後面跟過來的人,驚慌地張大眼,他希望他們知道原因,可是那些臉,一樣驚恐,他們沒有手機,他們之中只有古錢伯有手機,應該說,他們有很多手機,可是沒有一隻可以打,天未光,古錢伯不會那麼早出現。 沒有路燈的地方,夜色還稠得很,像寶藍色的粥,遠近的笑鬧、煙火和炮彈,剛睡。喇牙不知道阿瑛的手機號碼,阿瑛自己會來,有阿強在的地方阿瑛就會出現,可是死阿瑛這幾天都沒有出現。喇牙突然想哭,有些東西哽在後腦和喉頭,可是他根本忘記眼淚的滋味了,在這裡哭,會被笑死,那是肖查某肖查哺做的事,他向著捷運站的方向,又轉頭對著觀世音菩薩的方向,突然,他看到烈兒,什麼烈兒,那是阿瑛黑白取的怪名字,根本就是嘴瀾琴,嘴瀾琴一定有手機,也許有阿瑛電話,他知道嘴瀾琴不是想遇就遇得到,馬上衝了過去。 嘴瀾琴宿醉得厲害,全身酒臭,異味一股腦兒鑽進鼻孔,喇牙打了一個大噴嚏,眼淚奔了出來,後面就跟了更多的眼淚,他沒辦法說話,嘴瀾琴的嘴也臭,比平常吹完口琴甩出來的口水臭多了,他撥開他上衣口袋,又翻摸外套和褲檔兩邊的口袋。 草地那邊聚集了三、四個人,他聽到議論紛紛,關於阿瑛、炮妹、拉皮珍、古錢伯和養蟲仔的點點滴滴,像雨,落在那個橫躺的身軀上,他終於翻到手機了,通訊錄裡躺著一個「英」,他用力按下比米粒大一點的黑色撥出鍵。 一轉身,一個黑衣黑褲的身影閃現,已經走到馬路中間要上到這岸的人行道了,他有一種不好的預感,天上落下雨珠,接連好幾顆,他聽到語音信箱在講話,然後,長嗶一聲,他沒有留言過,不知道講下去阿瑛會不會聽到,這世上真有一種看不見的信箱,可以裝話給看得見的人? 喇牙對著手機,更像對著空氣,「阿瑛,阿強走了,你緊來!」
 受傷的勇士-王明道的一世紀
受傷的勇士-王明道的一世紀 BRAVE10S~真田十勇士S 6
BRAVE10S~真田十勇士S 6 鋼砲勇士 3
鋼砲勇士 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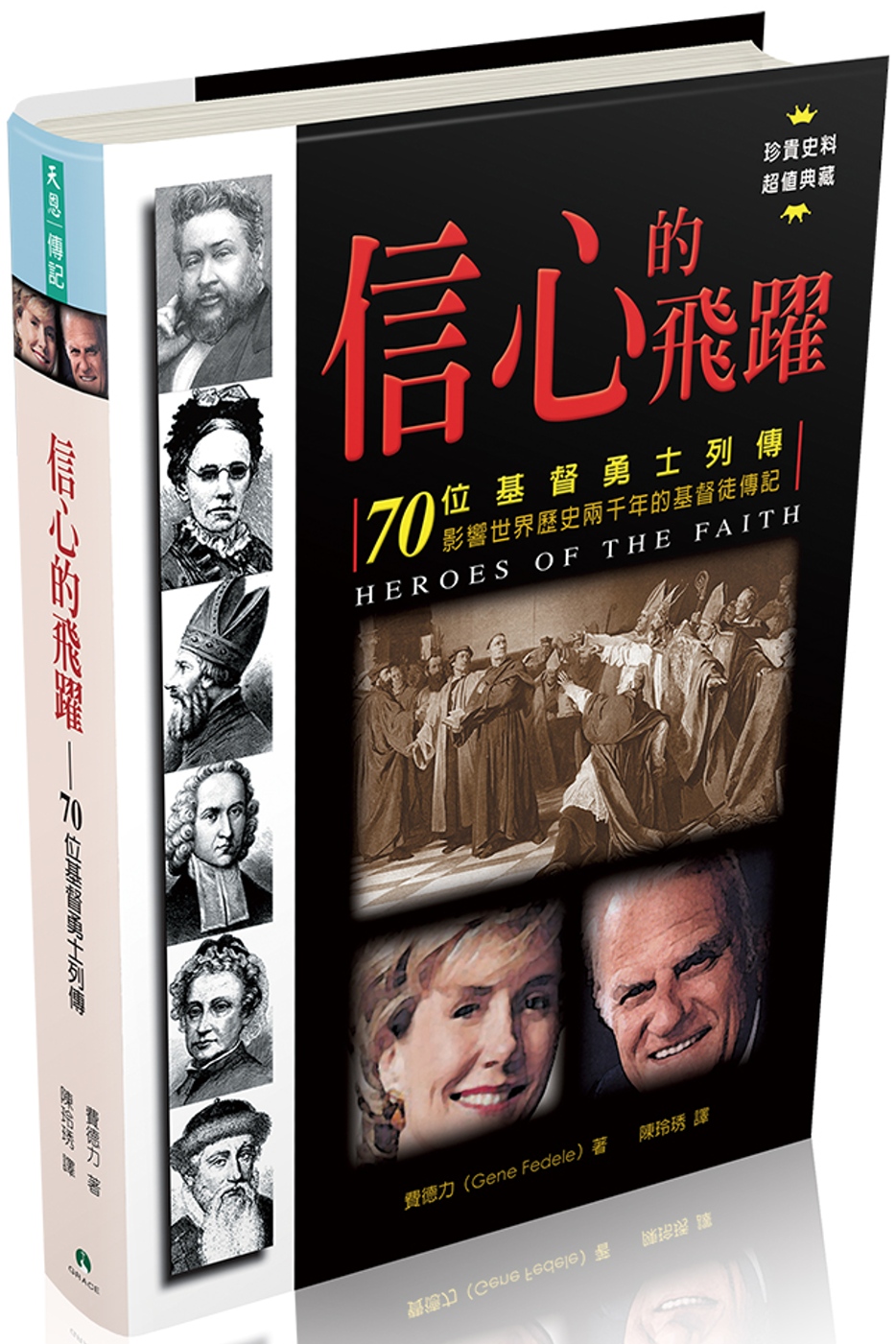 信心的飛躍:70位基督勇士列傳
信心的飛躍:70位基督勇士列傳 上床吧!我的勇士之一 悍妻如至寶
上床吧!我的勇士之一 悍妻如至寶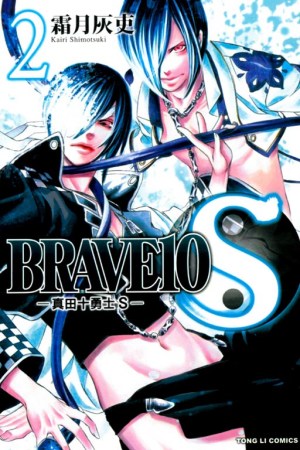 BRAVE10S~真田十勇士S 2
BRAVE10S~真田十勇士S 2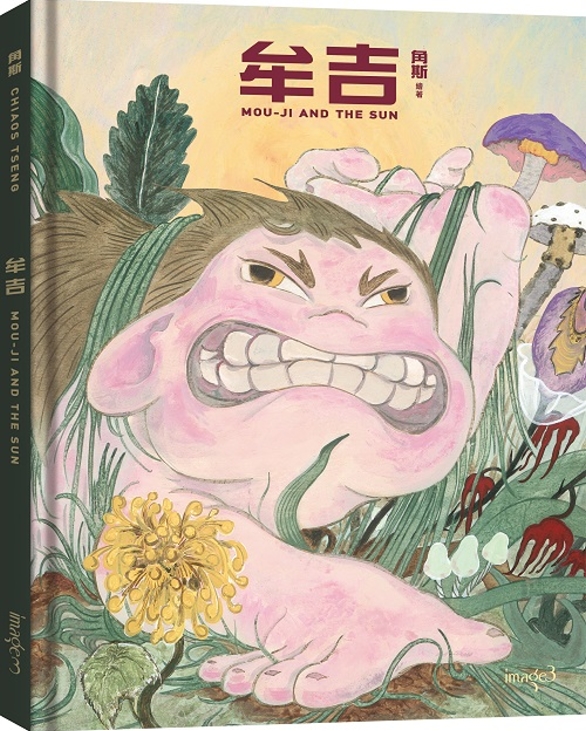 牟吉
牟吉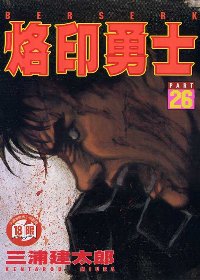 烙印勇士(26)
烙印勇士(26) 痞子勇士 8(完)
痞子勇士 8(完)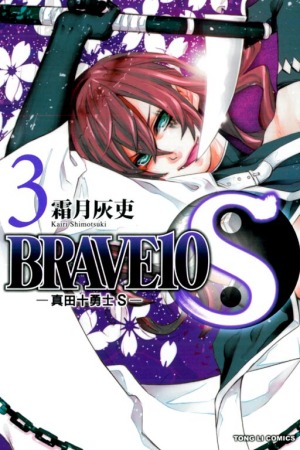 BRAVE10S~真田十勇士S 3
BRAVE10S~真田十勇士S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