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瑜伽與自然光的修習 | 運動資訊第一站 - 2024年11月

夢瑜伽與自然光的修習
人的一生有近三分之一時間處於睡眠狀態,而夢境反映的情景,即是我們在現實生活中所遭遇的渴望、恐懼和期待。
事實上,我們可以經由上師的帶領和指導,跳脫夢境的桎梏,認清夢不過是一種假象,進而在夢中修習,將夢境予以轉化,以增進自己心靈上的覺知。
《夢瑜伽與自然光的修習》摘自南開諾布仁波切的手稿資料,強調在作夢與睡眠狀態中發展覺知的特定練習,再予以擴展與深化。在此書中,南開諾布仁波切歸納了特定的方法,用以訓練、轉化、消融、攪亂、穩固、精煉、持守和逆轉夢境;此外,他還提出了個人持續在白天和夜晚所有時刻修行的練習,包含發展幻身的修習、為開發禪觀的甚深淨光修習,以及死亡之時遷轉神識的方法。
我們應該會被本書所描述的進階修習所鼓舞,儘管這個進程不會太快,但不可或缺的是,我們所有的人皆能仔細審視自己的能力,然後繼續前進。這可能是我們第一次必須努力試圖記起夢境,或更為進階地,則為轉化夢境。對於從事任何級別夢修練習的人而言,皆能開發出越來越多的天賦本能。
作者簡介
南開諾布仁波切
1938年10月8日生於東藏。兩歲時,由兩位禪修大師認證為阿宗珠巴的轉世。八歲時,被第十六世噶瑪巴和司徒仁波切認證為竹巴噶舉大師阿旺南喬的轉世。
南開諾布仁波切從八歲到十四歲,進入佛學院閉關修習,跟隨著名的上師一起學習,包括女性上師阿育康卓,那時她已經113歲高齡,仁波切從她那裡接受了眾多的傳承,並做了這些修法的密集閉關修習。
1954年,仁波切成為西藏青年代表,應邀前往漢地。從1954年開始,在四川成都的少數民族西南大學擔任藏文教師,並學習了漢語和蒙古語。
仁波切十七歲時,根據夢中獲得的一個淨觀,回到了德格的家,並去參見其根本上師蔣秋多傑仁波切,他從上師那裡,進一步接受了大圓滿精髓教法的灌頂和傳承。更重要的是,根據南開諾布仁波切所說,這位上師將他直接導入到大圓滿的經驗中。
1960年,仁波切二十二歲時,應圖齊教授的邀請,前往義大利羅馬居住了幾年。
從1964年到現在,南開諾布仁波切一直是那不勒斯大學東方學院的教授,教授藏文、蒙古文和西藏文化歷史。南開諾布仁波切在不同國家非正式地帶領傳法禪修,在這些禪修中,他以一種不分教派的形式,給予了大圓滿修法的教授,並教授幻輪瑜伽、藏醫和占星術。
南開諾布仁波切著有十多本大圓滿禪修書籍,包括《水晶與光道》(The Crystal and the Way of Light)和《日與夜的循環》(The Cycled of Day and Night)等。
譯者簡介
歌者
蘭州大學英語系,由南開諾布仁波切認證之一級金剛舞教師,及南卡教學與幻輪瑜伽合格老師。
編者前言
致謝
編者導論
第一章 夢的本質與類型
第二章 夜晚的修習
第三章 修習夢之精要的方法
第四章 幻身
第五章 淨光心髓的修習
第六章 明性之夢
第七章 遷識的方法
第八章 瑪拉替卡朝聖
第九章 南開諾布仁波切專訪
第十章 掌中佛法
第十一章 南開諾布仁波切生平簡介
導論
五○年代一個黑暗的晚上,我從自己床上狂奔到父母房門口,蜷縮在那裡,心有餘悸卻依然半睡半醒。我那時大概五歲,那個夢魘生動的影像至今仍記憶猶新。它看起來是如此真實:一條蛇盤繞在我的床上──儘管我的父母再三保證這只是一個夢,卻安撫不了我。
這是我最早的夢記憶之一。這個夢貫穿我整個童年和青少年時期,不斷重複又重複,甚至現在我已漸入中年還會偶爾出現。夢是什麼呢?一個關於蛇的夢不斷重複是否具有特殊涵義?或許蛇是潛意識的使者,抑或是兒童早期性的激發,還是與被稱為龍族(nagas,生活在水裡的蛇形眾生)的另一類型眾生的溝通?也許夢只能在夢者的生活脈絡中來解讀,因而具有特定的個人意義。
根據夢境工作(dreamwork)大師,原型素材(archetypal material)、個人的憂慮與關切、對未來的預知、與其他層面眾生的交流,在夢中都是可能的。然而,這項說法應修正為僅少數人遭遇這種範疇的夢經驗,對大多數人而言,作夢只是單純就夢者期望、恐懼與個性之脈絡內,白天印象的重新改寫。
在一九五○年代,儘管出現少數哲學家和當代思想家,對作夢持有新鮮的興趣,但對大多數美國人,包括我來說,檢視夢境並無太大意義。對這個主題漫不經心的狀態,很快就隨著六○年代的劇變而改觀。肇因於這十年的戲劇性變化,來自集體與個人危機的嚴峻考驗,以及同時期瑜伽和各種禪修形式的盛行,使得夢的覺知開始在大眾文化中,也在我自己身上重新發聲。
我對幼兒到大學時代的夢記憶已模糊,童年的鮮活影像和清晰記憶逐漸消逝為片斷、甚至不剩半點記憶,但在一九七八年,我對夢狀態的經驗與瞭解有了根本的轉變。當時我前往法國去跟知名的西藏喇嘛敦珠仁波切學習,在他所教授的主題當中有夢瑜伽,仁波切清楚地談到努力獲得覺知的需要甚至在睡眠狀態中亦然。他將人類目前的睡眠狀態和動物的無意識睡眠相比,痛惜人們浪費如此寶貴的機會發展自身。仁波切開示的帳篷裡有一種奇異的狀態,我所見和聽到的一切似乎都像夢一樣,毫無疑問是來自這位偉大喇嘛強大的傳承力量。我離開後,這種陌生的感知持續一整天直到晚上,而那晚也同樣不尋常。當我準備要去睡覺時,我決心按照仁波切的指導來發展覺知並祈請他的幫助。
我睡著了,但很快便意識到我正在睡覺,我是在一種有意識的光明狀態中躺著。這是我對瑜伽式睡眠和心之自然光第一次有意識的體驗。
由於我個人心的障礙,我並沒有在夢瑜伽和自然光的修習上取得很大的進步,事實上,如果不是曾經有過這樣的一次經驗,我很可能已經放棄整個關於瑜伽技藝領域的議題,而這種技藝超出普通人的能力。幾年後,在一次為期二十一天的單獨閉關中,我對瑜伽式作夢有了另一次的體驗,那著實令人興奮並具有轉化性。兩個星期過去後,我的閉關相當程度地更加深入,每晚我都按照敦珠仁波切的教導來發展夢瑜伽的能力,那時密集的禪修練習延長至一天十個小時,我的心變得更為有力,我很驚奇自己一晚能記得的夢竟然多達八個。
在這特別的一晚,我突然理解我在睡覺也是醒著──我正在作夢。一旦我體認這點的時候,夢中景觀的色彩變得驚人的生動和鮮豔。我發現自己站在懸崖邊,俯瞰一個廣袤美麗的山谷,我感到十分放鬆而激動,並提醒自己說,這只是一個夢。
飽覽這個怡人的風光一會兒後,我決定真實地且又虛幻地更進一步。如果這真的是一個夢,那麼就沒有理由我不能飛。我不是用飛的而是往空中一躍,但我發現夢又一次轉變。我仍是清明的,我的覺知出現在樓梯上,而我的身體卻不再處於夢中,但我正在上樓。我才剛踏上一階、正要跨到下一階時,此時夢境再度轉換。這次只有一片黑暗,沒有任何影象。我抗拒著想要去睜開眼睛的衝動,事實上,我不確定要如何做,但我希望也想要影像重新出現,然後突然間我回到那個樓梯上。樓梯重新出現只持續很短暫的時間,之後我便醒了。
整個經驗是如此驚奇,我一直認為這是我一生中最有意義的經歷之一,指導這次閉關的喇嘛將我的經驗比作已通過駕駛測驗。這之後我有許多夢中清明的經歷,我不能說每晚都會發生,但亦規律出現,在我進行密集禪修時,例如閉關,頻率就會增加。再者,如果我在夜裡醒來禪修,我發現再回去睡時我的清明夢會頻繁出現。
在此期間,我還作了些性質上屬於感應的夢。例如,在閉關中我夢到我的情人,儘管我在夢中並非清明,但是我記得很清晰:她的影像出現,她如此光輝明亮但卻在啜泣。
隔天我依計畫前往紐約上洲一個火車站接她,為了驗證我的夢經驗,我告訴她我為她前晚的心煩感到難過。她看起來很吃驚,立刻告訴我說這個夢是對的,她告訴我說她病倒了,而她的確哭得很傷心。
正如我所提到的,看來似乎是當我有機會練習禪修或夢瑜伽教法時,這些經歷便會增加。就是在我參加南開諾布仁波切於華盛頓特區研討會這樣的期間,他最資深的弟子之一陪同他前來,且病得很重。在我夢裡,我發現自己正跟南開諾布仁波切在一起,他非常關注這位弟子的健康危機。我說:「仁波切,她快死了。」仁波切回答道:「不,我已經治癒了她,她正好轉中。」隔天好消息就是她的確正在康復,但更為令人稱奇的是,南開諾布仁波切在我告訴他之前就已經知道我們夢中這段交談。之後我還作了南開諾布仁波切與我交談的其他的夢,偶爾我也會說一些智慧的話回答他。仁波切對這些經歷非常感興趣,有時隔天就會問我前晚是否作了一個有意思的夢;偶爾他會問我而如果我記不太清楚時,他就會說:「你必須記得,你必須嘗試去記得啊!」
導論 五○年代一個黑暗的晚上,我從自己床上狂奔到父母房門口,蜷縮在那裡,心有餘悸卻依然半睡半醒。我那時大概五歲,那個夢魘生動的影像至今仍記憶猶新。它看起來是如此真實:一條蛇盤繞在我的床上──儘管我的父母再三保證這只是一個夢,卻安撫不了我。 這是我最早的夢記憶之一。這個夢貫穿我整個童年和青少年時期,不斷重複又重複,甚至現在我已漸入中年還會偶爾出現。夢是什麼呢?一個關於蛇的夢不斷重複是否具有特殊涵義?或許蛇是潛意識的使者,抑或是兒童早期性的激發,還是與被稱為龍族(nagas,生活在水裡的蛇形眾生)的另一類型眾生的溝通?也許夢只能在夢者的生活脈絡中來解讀,因而具有特定的個人意義。 根據夢境工作(dreamwork)大師,原型素材(archetypal material)、個人的憂慮與關切、對未來的預知、與其他層面眾生的交流,在夢中都是可能的。然而,這項說法應修正為僅少數人遭遇這種範疇的夢經驗,對大多數人而言,作夢只是單純就夢者期望、恐懼與個性之脈絡內,白天印象的重新改寫。 在一九五○年代,儘管出現少數哲學家和當代思想家,對作夢持有新鮮的興趣,但對大多數美國人,包括我來說,檢視夢境並無太大意義。對這個主題漫不經心的狀態,很快就隨著六○年代的劇變而改觀。肇因於這十年的戲劇性變化,來自集體與個人危機的嚴峻考驗,以及同時期瑜伽和各種禪修形式的盛行,使得夢的覺知開始在大眾文化中,也在我自己身上重新發聲。 我對幼兒到大學時代的夢記憶已模糊,童年的鮮活影像和清晰記憶逐漸消逝為片斷、甚至不剩半點記憶,但在一九七八年,我對夢狀態的經驗與瞭解有了根本的轉變。當時我前往法國去跟知名的西藏喇嘛敦珠仁波切學習,在他所教授的主題當中有夢瑜伽,仁波切清楚地談到努力獲得覺知的需要甚至在睡眠狀態中亦然。他將人類目前的睡眠狀態和動物的無意識睡眠相比,痛惜人們浪費如此寶貴的機會發展自身。仁波切開示的帳篷裡有一種奇異的狀態,我所見和聽到的一切似乎都像夢一樣,毫無疑問是來自這位偉大喇嘛強大的傳承力量。我離開後,這種陌生的感知持續一整天直到晚上,而那晚也同樣不尋常。當我準備要去睡覺時,我決心按照仁波切的指導來發展覺知並祈請他的幫助。 我睡著了,但很快便意識到我正在睡覺,我是在一種有意識的光明狀態中躺著。這是我對瑜伽式睡眠和心之自然光第一次有意識的體驗。 由於我個人心的障礙,我並沒有在夢瑜伽和自然光的修習上取得很大的進步,事實上,如果不是曾經有過這樣的一次經驗,我很可能已經放棄整個關於瑜伽技藝領域的議題,而這種技藝超出普通人的能力。幾年後,在一次為期二十一天的單獨閉關中,我對瑜伽式作夢有了另一次的體驗,那著實令人興奮並具有轉化性。兩個星期過去後,我的閉關相當程度地更加深入,每晚我都按照敦珠仁波切的教導來發展夢瑜伽的能力,那時密集的禪修練習延長至一天十個小時,我的心變得更為有力,我很驚奇自己一晚能記得的夢竟然多達八個。 在這特別的一晚,我突然理解我在睡覺也是醒著──我正在作夢。一旦我體認這點的時候,夢中景觀的色彩變得驚人的生動和鮮豔。我發現自己站在懸崖邊,俯瞰一個廣袤美麗的山谷,我感到十分放鬆而激動,並提醒自己說,這只是一個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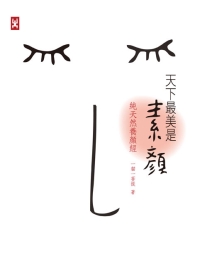 天下最美是素顏(純天然養顏經)
天下最美是素顏(純天然養顏經) 讓你超逆齡,健康又美麗套書(超逆齡...
讓你超逆齡,健康又美麗套書(超逆齡... 活力迎接更年期,下半生更健康:強化...
活力迎接更年期,下半生更健康:強化... 瑜伽晨練
瑜伽晨練 晨型人的新生活實踐術
晨型人的新生活實踐術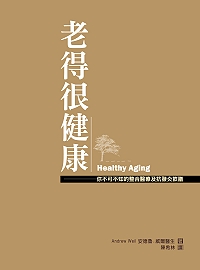 老得很健康──你不可不知的整合醫療...
老得很健康──你不可不知的整合醫療... 安眠,藥不要:不需藥,不夜醒,躺下...
安眠,藥不要:不需藥,不夜醒,躺下... 眩暈、耳鳴對症導航
眩暈、耳鳴對症導航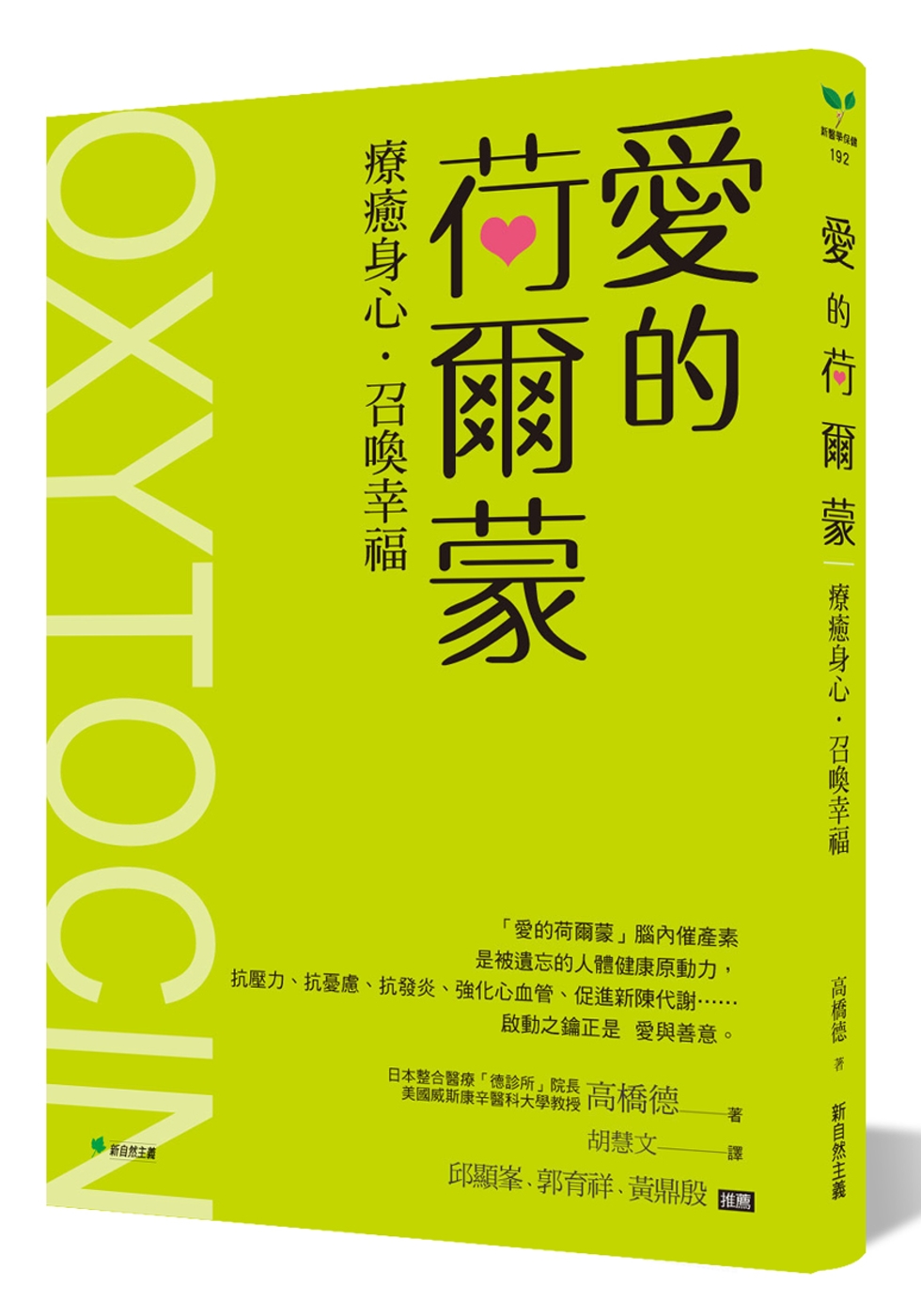 愛的荷爾蒙:療癒身心‧召喚幸福
愛的荷爾蒙:療癒身心‧召喚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