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獵犬號航海記(上下冊合售) | 運動資訊第一站 - 2024年1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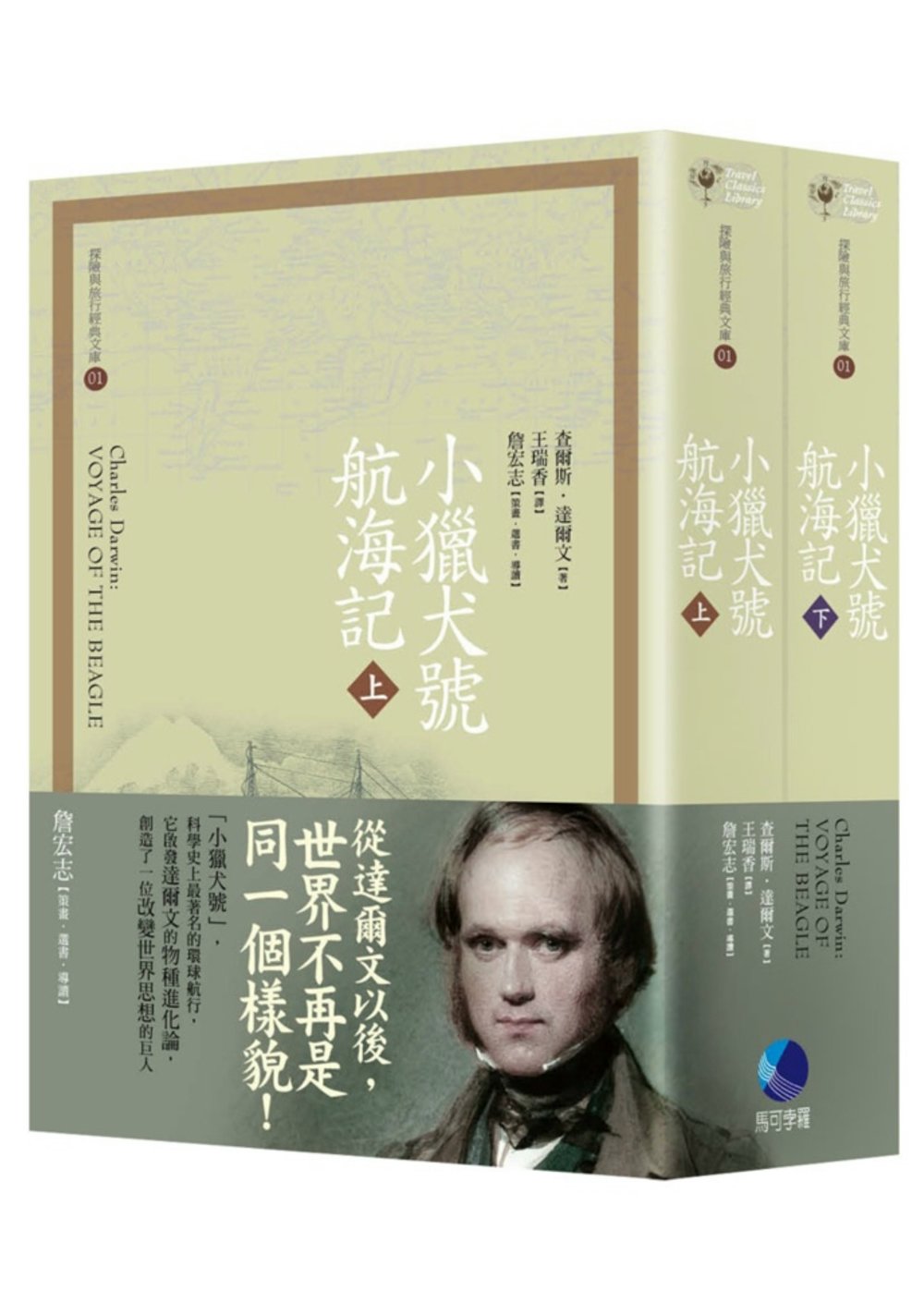
小獵犬號航海記(上下冊合售)
從達爾文以後,世界不再是同一個樣貌!
「小獵犬號」因為載運了達爾文這位意外的乘客,而永垂不朽;
這趟環球航行也成了科學史上最著名的旅行;
它啟發了達爾文的物種進化思想,也改變了整個世界
一八三一年十二月,達爾文以船長隨伴身分登上英國海軍艦艇「小獵犬號」,航離祖國,開始為期五年之久的環球科學考察之旅。當時達爾文不過二十三歲,剛從劍橋大學畢業,對生物學和地質學所知有限,然而,當一八三六年十月「小獵犬號」回到英國時,他卻已成了這些領域中的佼佼者。更甚者,透過這場航行所做的自然觀察,他在二十年後發展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革命性演化理論,對人類社會產生深遠影響。
達爾文無疑是一流觀察家,他鉅細靡遺地描述了沿途所見動植物、地質、部落等,用筆生動有趣,在邏輯推演和科學思維上更是超強,絕對史無前例。透過這本《小獵犬號航海記》,你可享受由達爾文親筆紀錄的這場精采冒險之旅,更可見識到第一流科學產生的迷人過程。
在阿根廷,達爾文發現類似現代物種的已滅絕動物的化石;在加拉巴哥群島,達爾文注意到此島群上與南美洲大陸上的同種動植物卻擁有許多相異點,還發現喙形上呈現幾近完整演化各階段的一群雀,這些發現是他日後重要學說演化論的奠基。穿越太平洋期間,他發展出有關珊瑚圓丘如何形成的理論,結果與現行理論完全吻合……
此書於一八三九年出版,之後達爾文陸續修訂內容,其中以一八四五年的第二版最為著名。然而,與其提供這些修訂過的、較晚後的版本,更重要的是呈現出版的文本,俾能盡可能準確地掌握達爾文在航行期間所經歷的思考與冒險過程。故刊於此的正是最原始版本的中文全譯本,當時的達爾文尚未推演出演化論,著墨更多的是旅程中所見的一點一滴,有奇特的動植物、火山、海嘯、化石、熱帶雨林、地震、異國風情、難得一見的海上風光等等。當你細讀達爾文描述南美印第安人的流星錘和拉索絕技、大溪地土著互相摩擦鼻子的打招呼方式,以及加拉巴哥群島上數之不盡的笨重大陸龜等等,眼前絕對會浮現栩栩如生的景象,令你拍案叫絕。
作者簡介
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
英國博物學家,演化論原創者。一八O九年誕生於英國的舒茲伯利(Shrewsbury),在舒茲伯利學校、愛丁堡大學和劍橋大學基督院受教育。他在一八三一年取得文學士學位,同年,以船長隨伴的身分登上小獵犬號,展開為期五年的環球航行之旅。這場航行有兩個主要目的,一是畫出巴塔哥尼亞和火地島海岸圖,二是帶回全球一連串有關時間的科學測定資料。在他尚未結束航程前,他部分牽涉到科學論題的信件已被私下發表,於是他一返國,立刻成為科學界的名人。
一八三九年,他被推舉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之後他繼續撰寫並發表這場航行中的發現,並努力蒐集材料驗證他的物種演化理論。一八五九年,他終於發表了《物種起源一書》,提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見解,暗喻人類是猿猴的後裔,這革命性理論立刻引起熱烈爭議。
此後,他偕同一八三九年迎娶的表姊艾瑪‧維吉伍德及孩子們,長年住在他們坐落於英國肯特郡的「唐恩居」。他於一八八二年辭世,以英國最高榮譽之尊被埋葬在倫敦西敏寺。
相關著作
《小獵犬號航海記》
譯者簡介
王瑞香
國立台灣大學哲學學士,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人類學碩士。曾任中時報系編譯、撰述委員,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誠品閱讀》主編。現任輔大翻譯學研究所兼任講師,婦女新知基金會顧問,並從事自由創作、翻譯、自然寫作、自然生態影片特約劇本撰寫等。
著作有《一個女人的感觸》;譯作包括《地圖師之夢》、《環境倫理學》、《內在革命》、《卡蜜兒》等。
編輯前言
導讀 達爾文的旅程──小獵犬號航海記 /詹宏志
作者序
第一章 佛得角群島的主島聖牙哥
第二章 里約熱內盧
第三章 馬爾多納多
第四章 內格羅河到布蘭卡港
第五章 布蘭卡港
第六章 從布蘭卡港到布宜諾斯艾利斯
第七章 從布宜諾斯艾利斯到聖菲
第八章 班達歐里恩塔
第九章 巴塔哥尼亞
第十章 聖克魯斯至巴塔哥尼亞
第十一章 火地島
第十二章 火地島到福克蘭群島
第十三章 麥哲倫海峽
第十四章 智利中部
第十五章 奇洛埃島與喬諾斯群島
第十六章 奇洛埃島與康塞普西翁
第十七章 安地斯山通道
第十八章 智利北部秘魯
第十九章 加拉巴哥群島
第二十章 大溪地與紐西蘭
第二十一章 澳大利亞
第二十二章 珊瑚層
第二十三章 從模里西斯到英國
附錄一 達爾文年表
附錄二 英國海軍部隊小獵犬號的指示
附錄三 羅伯‧費茲洛伊「關於大洪水的看法」
附錄四 首版補遺
導讀
達爾文的旅程——小獵犬號航海記 詹宏志
一八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從英國樸立茅茨港(Plymouth)駛出一艘並不特別起眼的三桅帆船,全長不過九十呎,載重二百四十二噸,比起它即將創造的歷史聲名,它的外表可算是有點寒酸。
這是一艘即將前往南美洲的科學考察船,名號為「小獵犬號」(HMS Beagle),隸屬於英國海軍的「水文測量局」(Hydrographer’s Office),由雄心勃勃的年輕艦長羅伯.費茲洛伊(Robert FitzRoy, 1805-1865)所率領,探險考察的航程計畫是兩年,但等到「小獵犬號」再回到英國港口的時候已經是一八三六年十月二日,整整過了五十八個月。
船上連艦長在內共有七十四人,除了各種職司的船員之外,還包括了不在編制內由艦長自掏腰包聘任的兩位雇員,一位是儀器工匠,一位則是畫家(他負責繪製沿途所歷所見,功能相當於今天的攝影師);還有三位順道返鄉來自火地島(Tierra del Fuego)的土著(他們是前一次「小獵犬號」科學考察採集回來的「標本」),以及一位自願護送他們回家的傳教士;此外,船上還有另一位不速之客,那就是被艦長邀請上船與他相伴,自己必須負擔所有旅費的年輕自然學者:二十二歲的劍橋大學畢業生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即後來以《物種源始》(The Origin of Species, 1859)一書改變全世界思想的作者。
你可以說,「小獵犬號」因為載運了達爾文這位意外的乘客而名垂不朽,連帶這趟旅行也成了科學史上最著名的旅行;但你也可以說,因為達爾文上了「小獵犬號」,這趟旅行改變了他和他的思想,進而使他改變了全世界。總之,就像史蒂芬.杰.顧德(Stephen Jay Gould)在他著名的書名所暗示的,「自從達爾文以後」(ever since Darwin),世界就不再是同一個面目了。
「小獵犬號」的艦長費茲洛伊為什麼要邀達爾文上船?因為前一任「小獵犬號」船長是自殺身亡的,而出身海軍世家的費茲洛伊,他的父執輩也有海上自殺的紀錄。維多利亞時代,海上階級森嚴,船員不能與艦長同桌吃飯,談話也有一定的禮儀和模式,艦長固然是海上的上帝,但卻道道地地是一位孤獨的上帝;費茲洛伊是上流社會出身的海軍菁英,擁有良好的科學知識與軍事訓練,他深知海上長期孤絕與精神沮喪的風險,遂想邀請一位出身與他相當的「紳士」(a gentleman),最好有相同的科學興趣,並能與他平起平坐,同桌進餐(但絕對,絕對不可以動他的儀器)。這個邀請透過劍橋大學的學術網絡,迅速來到達爾文的老師漢斯婁(John S. Henslow, 1796-1861)的手中,希望他能推薦一位合適的年輕人,漢斯婁在一八三一年八月二十四日寫信給達爾文說:「我相信你是他們想要找的人。」
但達爾文為什麼要接受這樣的邀請,付出那麼大的代價上船(他光是買儀器就花了六百英鎊,那是他兩年在劍橋大學的全部費用)?這就要追溯到「科學考察旅行」的歷史了。
比達爾文早一個世紀的科學考察航行,多半是出於軍事目的,譬如最著名的庫克船長(Captain James Cook, 1728-1779)的三次環球航行,他本來是被派到大溪地島(Tahiti) 去測量金星的軌跡,這是典型的海軍測量,目的是要正確描繪海洋的航道。如果英國能夠掌握全世界海洋的水文資料,英國海軍就能有效地控制世界;科學知識、海軍實力、帝國主義在這裡加起來共同構成一個超強經濟霸權。庫克船長不僅在地理上有很大的發現與貢獻,也讓澳洲和紐西蘭成為英國的殖民地,實質增強了英國的國力,也給這樣的科學考察旅行一個合理的投資報酬範例。然而在一七六八年庫克船長第一次航行時,「努力號」(Endeavour)上另有一位旅客,那就是自然學者約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1743-1820),他隨船所採集的植物標本成為他重要的學術資產,後來做了四十二年的英國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的會長,對後來有心學術的自然學者是一個很大的啟發。
比班克斯晚一代的自然學者都已經明白,「遠距旅行」是自然學者有效的學術晉身之階,因為遠離歐洲的地方提供了各形各色的奇花異草、眩人目光的珍禽異種,裡頭蘊藏無數可能的新分類和新啟發。和達爾文同世代的重要自然學者,幾乎都有他們自己的旅行,達爾文上了前往南美洲的「小獵犬號」,約瑟夫.虎克(Joseph D. Hooker, 1817-1911)則隨船參加了羅斯(James C. Ross, 1800-1862)的南極探險,湯瑪士.赫胥黎(Thomas Huxley, 1825-1895)也上了考察澳洲的「響尾蛇號」(Rattlesnake),他們全是出門旅行的人。
這也帶給旅行史上一個「新物種」:科學旅行家(scientific travellers)。從十九世紀開始,他們有意識地不斷發現新物種,為全世界的物種做清冊目錄,想把地球上的生物全貌掌握在手中,就像海軍孜孜不倦於繪製海圖一樣,他們行走世界各角落,努力把蒐羅來的物種納入林奈分類體系(Linnean system)裡頭,一種近乎重建《創世紀》的工作。
這其中,最富代表性的人物可能是世紀初的德國科學旅行家洪堡 (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1859),他以繼承的龐大財富資助自己五年的南美洲考察旅行,採集了無數前所未見的標本,寫下了三十卷的浩翰鉅著《新大陸赤道地區之旅》(Relation historique du voyage aux regions equinoxiales du nouveau continent, 1807-1834);其中,第二十八到三十卷是所謂的《個人記述》(Personal Narrative),也就是遊記的部分,這是當時轟動歐洲、影響深遠的旅行書。達爾文的「小獵犬號之旅」,全程隨身帶著洪堡的書,他更在家書中讚歎說:「我從前欣佩洪堡,如今我簡直是仰慕他;一進入熱帶地區,所有你心中挑起的感受他幾乎都提到過。」
這些記錄全世界物種的工作,在達爾文上船時,其實也即將盛極轉衰;林奈體系下物種的認識與分類,也已經到了尾聲,科學家下一步想知道的,不是「什麼」,而是「為什麼」,要有人能夠給這些龐大的新發現的全球物種資料,一個有意義的統合性解釋。而這件改變人類思想的工作,也將在達爾文下船後展開。
我們沒有辦法想像,如果達爾文因為某種緣故沒有搭上「小獵犬號」,是否他還會發展出他的「通過自然選擇的演化論」,進而影響了全世界?(這個可能性是隨時存在的,一開始,達爾文的父親並不同意他上船,而達爾文也幾乎放棄了;出發之後他又暈船得厲害,船長費茲洛伊不得不答應,在第一個停泊港口就讓他回家。)是否另一位發展出「演化論」的自然學者亞爾佛德.羅素.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 1823-1913)將是我們今天知道的「演化論」唯一發明者?
但我們確實知道,上船前和下船後的達爾文幾乎是不同的兩個人。年輕的達爾文是一位活潑、貪玩、花錢無節制的「阿舍仔」(但對知識與大自然充滿毫不矯情的研究熱情);即使在上了「小獵犬號」之後,船上嚴厲殘酷而不人道的紀律(譬如鞭笞水手)多少嚇到了他,但並沒有改變太多他的性情,他在旅途中寫給家人與老師的信仍然洋溢著頑皮的口吻,他還在加拉巴哥群島上試騎著名的大海龜(他說騎起來很不穩),頑童的身影還躍然紙上。
五年後下船的達爾文,或者更正確的說,已經形成「演化論」觀點的達爾文,卻是另一個終其一生努力不懈、不苟言笑嚴肅的達爾文。這個性格的大轉變是怎麼來的?「演化論」發現,眾多生物並不是如所說的「各從其類」,相反地,它幾乎每一世代都在變;生物通常會產出超乎足以生存的下一代,而它們之間常有微小的差異(也就是所謂的「突變」),在變化多端的自然環境的考驗下,有些差異的物種會比它們的同種更容易適應生存,就使得帶有某種特質的物種被保存下來。達爾文雖然沒有直接說人類是否適用這項規律(他是刻意迴避這個爆炸性的敏感問題),但思想的巨彈已經投下了。
寫下包含「演化論」草稿的達爾文,並沒有出版他的書或論文,反而把它藏在抽屜裡,旁邊還放了一筆錢,他要妻子以這筆錢把書出版,如果他生前未能見到的話。可見達爾文是完全明白自家理論的破壞性的,也許正因為他明白自己所發現的是劃時代的觀念,也明白它將帶給世界原有信仰的不安,使他晚年變得肅穆莊重,他不太為自己辯護,也沒有娛樂和社交,只是加倍沈默工作。我們也許可以稱這是達爾文「生命中不可承受的沈重」。
如果達爾文沒有登上「小獵犬號」,他也許不是影響世界的思想巨人,但他可能是比較輕鬆快樂的人。
一八三二年一月十六日──從海上看去,普拉亞港(Porto Praya)一帶顯得有些荒涼。過去長年來的火山高溫和熱帶烈日,已使大部分地方的土壤失去肥力、不適合植生。鄉間是層層高昇的台地,間有幾處削平的圓錐形山丘,地平線盡頭則是一列形狀不規則而較高的山嶺。從此地氣候所造成的煙霧中望去,收入眼裡的景觀極為動人;當然,這樣說是先有這樣的假定:一個剛從海上登陸、首次走過一片椰子樹的人,除了他自己的快樂之外還能對其他事物作出判斷。一般人會覺得這座島索然無味;然而,對任何一個只熟悉英國地景的人來說,一塊全然荒瘠的土地所顯現的新貌,卻具有一種壯麗之美──如果多了些草木反而會破壞這種美。在幾大片由冷卻的熔岩所構成的平原上,幾乎看不到任何綠葉;但是,幾群山羊和幾隻牛仍然有辦法在此存活。下雨的機會很少,但一年中有一段短暫時期會有傾盆大雨,隨之,稀疏的草木便會馬上從每個縫隙中長出。這些草木很快就枯萎了;動物便以這自然形成的乾草為食。就目前來說,已經整整一年沒有下過雨了。寬闊、平坦的山谷在雨季中多半只有幾天會成為河道,現在則長著一叢叢無葉的灌木。這些山谷裡生物很少。最常見的鳥是一種翠鳥(Kingfisher,學名Dacelo jagoensis);牠們安靜地停在蓖麻的樹枝上,從那裡快速啄食蚱蜢和蜥蜴。這種鳥羽色鮮豔,但不像歐洲種那麼美麗;在飛行姿勢、行為舉止、棲息地點──通常是在最乾燥的山谷──等方面,牠們也與歐洲種差異極大。 有一天,兩位軍官與我騎馬到里貝拉格蘭(Ribeira Grande),這是一個位於普拉亞港東方數哩外的村落。直到我們抵達聖馬丁(St. Martin)山谷之前,鄉間呈現的是常見的單調褐色景象;但一到了那裡,即見一條很小的河的河畔長著令人心怡的茂密草木。一小時之後,我們抵達大里貝拉,驚見一座大型碉堡兼教堂的廢墟。在它的海港淤塞之前,這小鎮是島上的主要聚落;現在它顯得陰鬱,但仍相當有景致。我們找了一位黑人神父作嚮導,也找了一個曾在半島戰爭中服役的西班牙人當翻譯;然後,我們造訪了一簇屋舍,其中最主要的建物是一座古老的教堂。佛得角群島(Cape de Verd Islands)過去的總督和司令就葬在這裡;有些墓碑上寫的是十六世紀的日期。
 腰痠背痛的人最需要的「修復瑜伽」:...
腰痠背痛的人最需要的「修復瑜伽」:...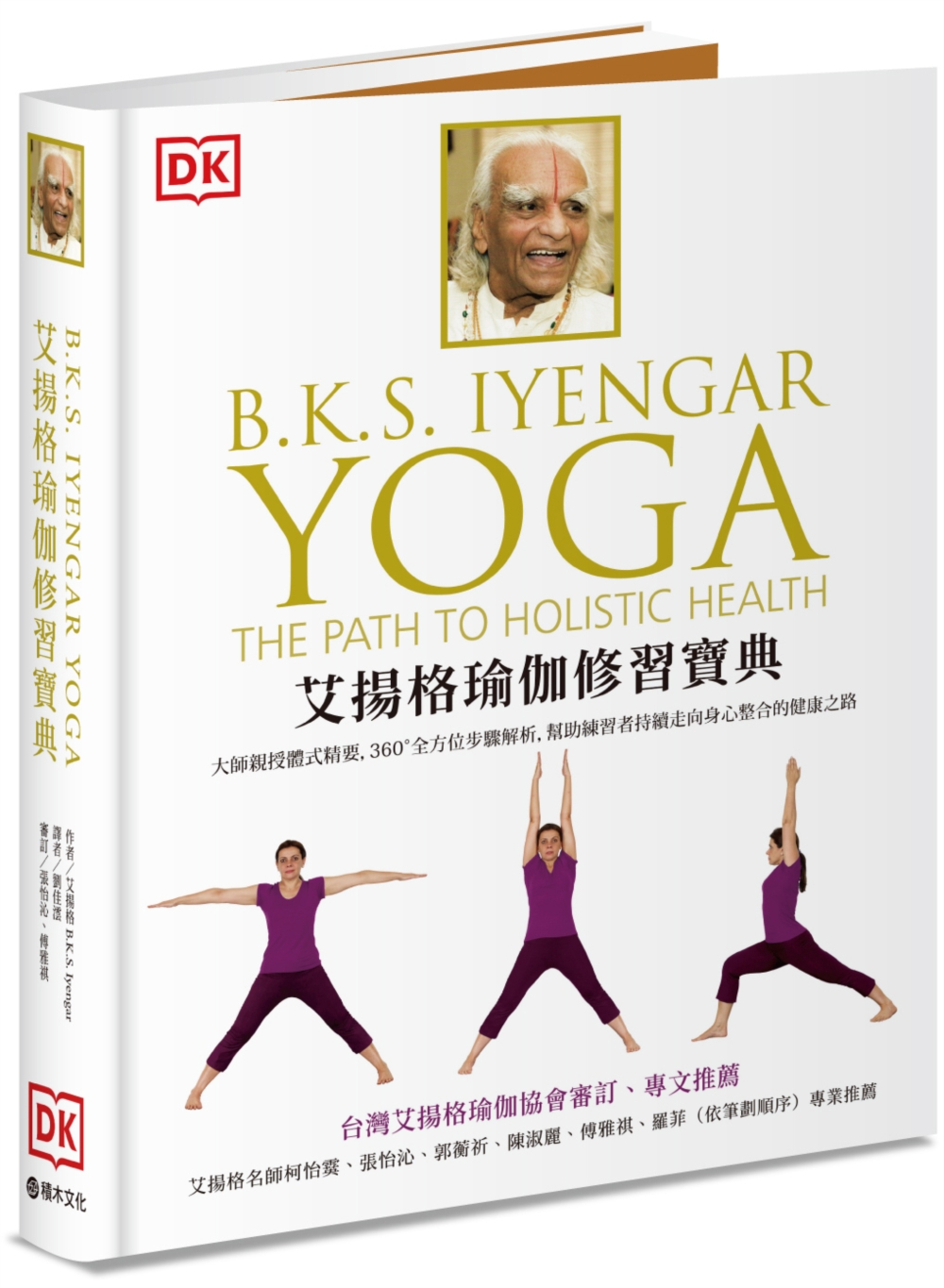 艾揚格瑜伽修習寶典:大師親授體式精...
艾揚格瑜伽修習寶典:大師親授體式精...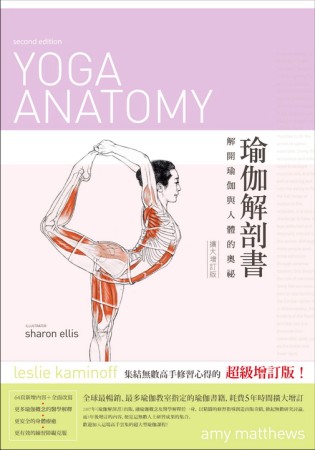 瑜伽解剖書:解開瑜珈與人體的奧祕(...
瑜伽解剖書:解開瑜珈與人體的奧祕(... 靈修訓體與瑜伽的精采對話:靈動、脈...
靈修訓體與瑜伽的精采對話:靈動、脈... 瑜伽解剖學:體式全彩圖解
瑜伽解剖學:體式全彩圖解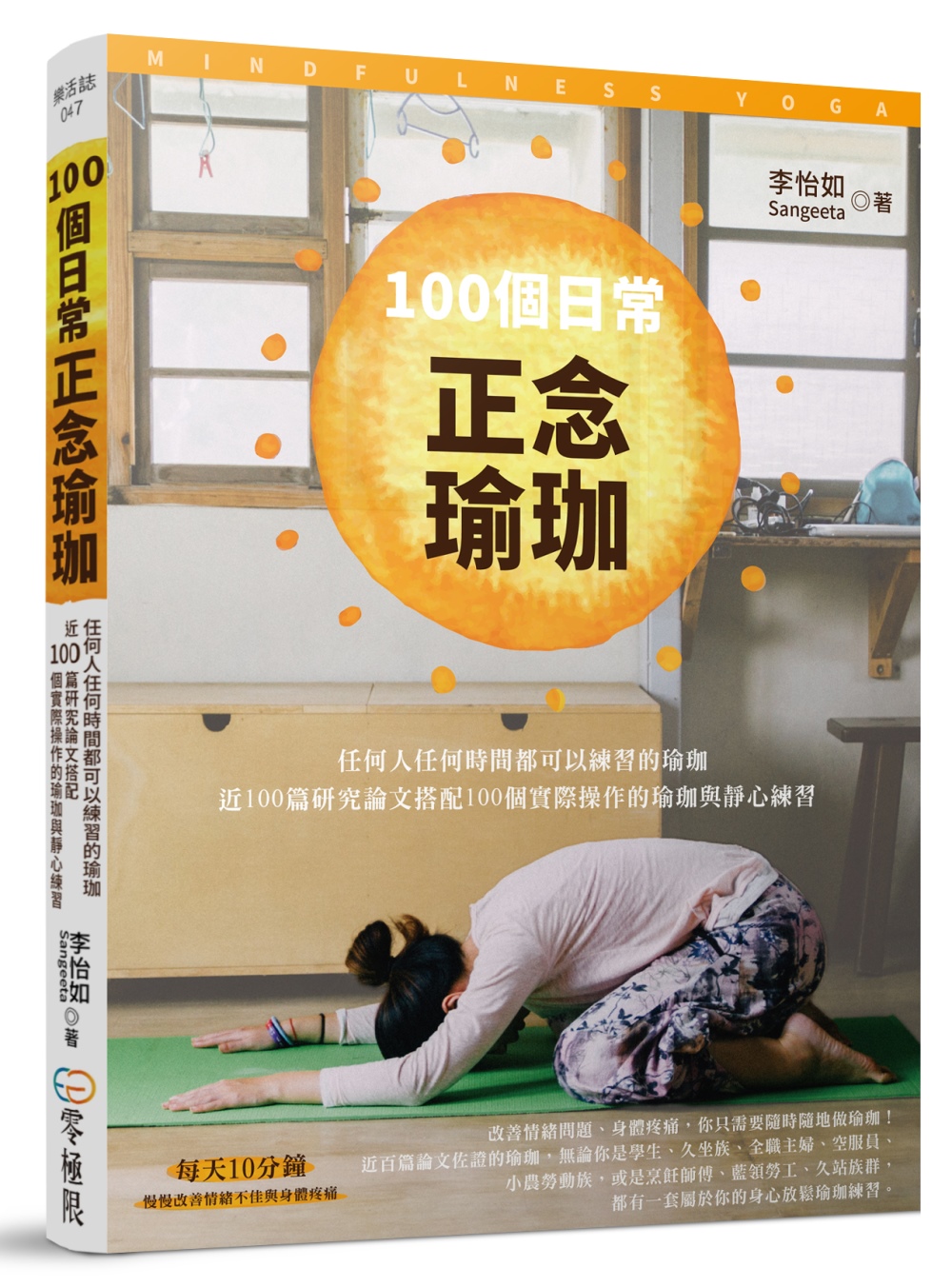 100 個日常正念瑜珈:任何人任何...
100 個日常正念瑜珈:任何人任何... 瑜伽,遇見真我的進行式(附「輕柔做...
瑜伽,遇見真我的進行式(附「輕柔做...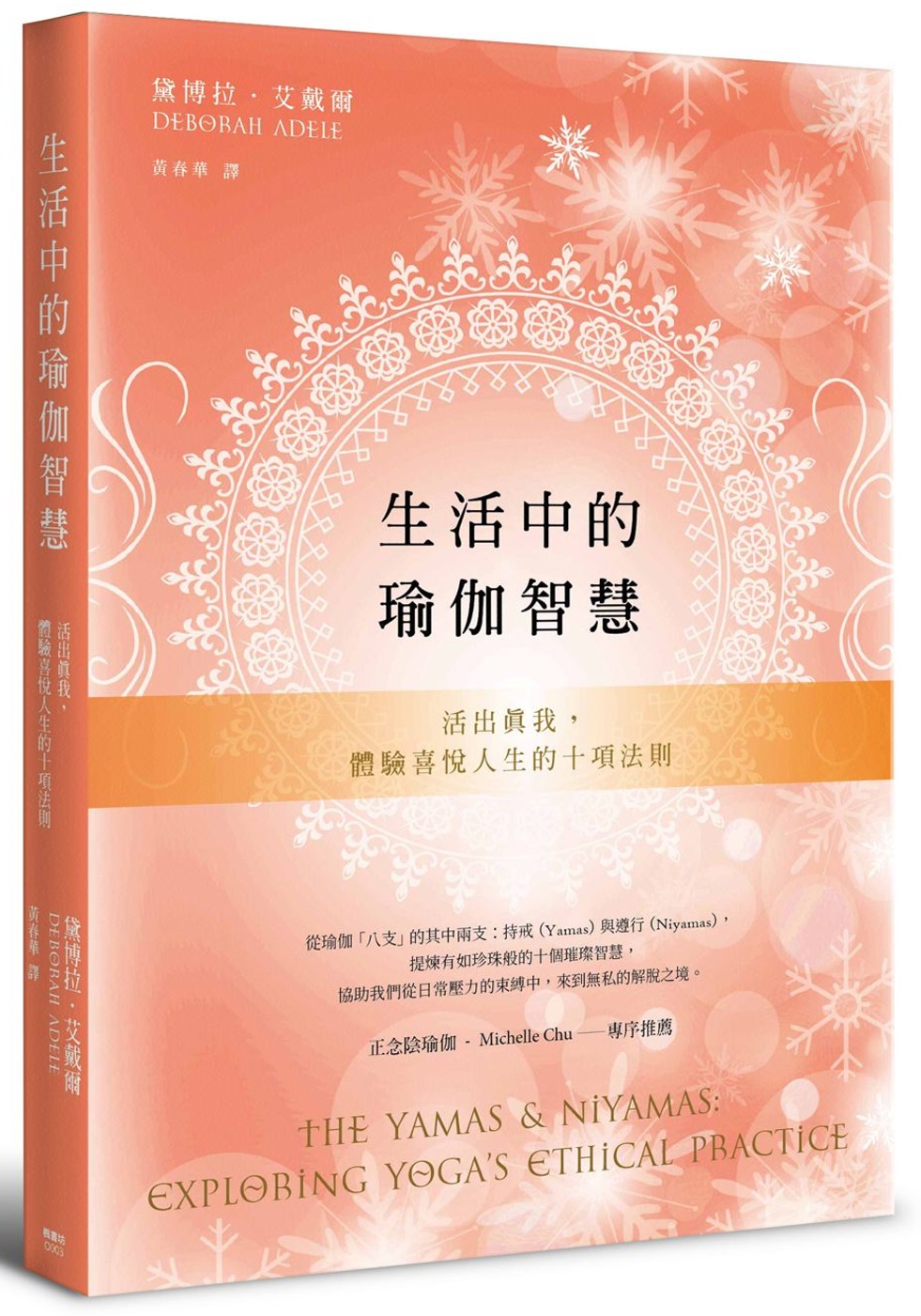 生活中的瑜伽智慧:活出真我,體驗喜...
生活中的瑜伽智慧:活出真我,體驗喜... 峇里島樂活瑜珈30式
峇里島樂活瑜珈30式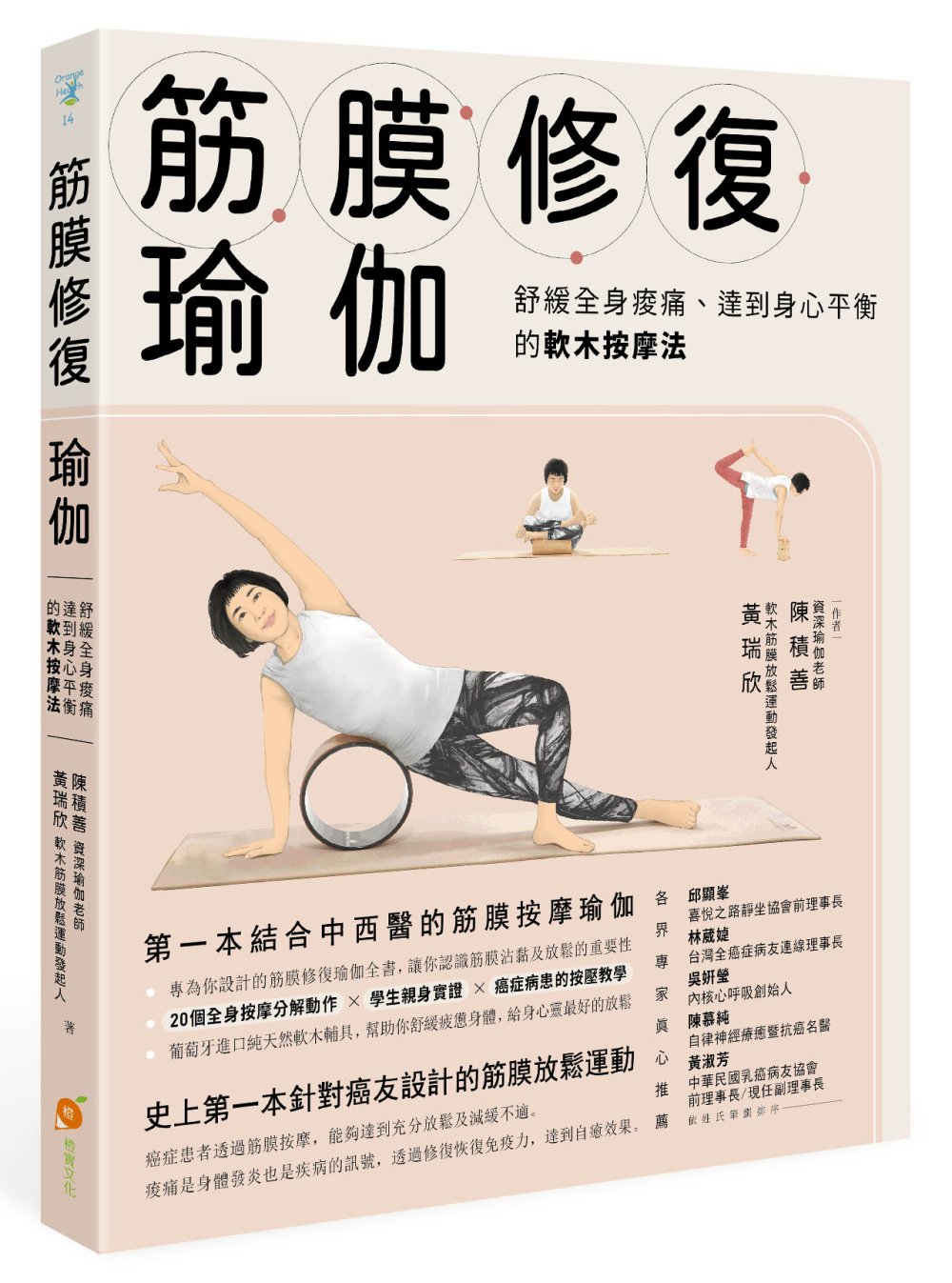 筋膜修復瑜伽:舒緩全身痠痛、達到身...
筋膜修復瑜伽:舒緩全身痠痛、達到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