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月澎湖(新版) | 運動資訊第一站 - 2024年11月

井月澎湖(新版)
西元1895年,清廷簽訂馬關條約,割臺、澎與日。時代動盪決定小人物的悲劇命運,澎湖許、李兩家族的興衰糾葛見證浮亂的時代苦況。作者藉人物李蓮子敘述兩家族的悲歡喜怨;從世代的遞嬗、時勢的流變道盡人世興衰及人性轉變。其間有切實動人歷史之真、溫柔敦厚親情之善及樸實精緻台語之美!寫時代也寫人性,寫家族也寫個人成長,是一部值得再三品味的台灣小說!
本書特色
井月澎湖是以澎湖家族興衰為著墨點的真實小說,此書出版後榮獲吳濁流文學獎、高雄文藝獎
作者簡介
李秀
袓籍澎湖,出生於台灣高雄市。興趣音樂、專長鋼琴,偶爾畫水彩。台灣小說、散文、童詩、新詩、歌詞作者。思念親情、探討愛情、關心社會。2002年以作家身分移民加拿大,為讓更多族群了解故鄉,特英譯出版”Penghu Moon in the Well (井月澎湖)”。目前從事英文、台文、華文及英譯工作,至2012年出版12本書。得過三屆高雄市文藝獎、吳濁流文學獎、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台灣省新聞處獎勵優良讀物、宏揚樂教獎、香港職青文藝獎、府城文學獎、高雄文學創作獎、打狗□邑新詩首獎等十幾獎項。
自序兼新版序 只為尋找井底那片月光 李秀∕10英文版自序 讓我奉獻一些濃蔭給您 李秀∕14華文版評介 重返童夢的故地 無葉∕19英文版評介 聯繫在同甘共苦之中Barbara Ladouceur∕31序幕∕35
Chapter 1 井月(1894-1922)∕37 火煲生活∕38黎一仁∕45許家情怨∕49金瓜拆灶∕55水燈∕60一井水一世人∕65
Chapter 2 外垵情事(1923-1928)∕71暗窩∕72金瓜冤∕78返鄉做大人∕86女願媳心∕95
Chapter 3 入船高雄(1929-1939)∕107李子天∕ 108空房騷動∕116李子山∕125勞碌鴛鴦∕132
Chapter 4 顛倒歲月(1940-1946)∕ 141風露草枝∕142澎湖兄妹眼中的日本人∕151空襲下的生死疏開∕161
Chapter 5 浮亂港都(1947-1954)∕173殘月他鄉∕174遺忘父祖的人子∕184打狗受難∕195死之花攀爬在心圃頂∕207
Chapter 6 童夢的故地(1955-1986)∕215分家爭產∕ 216韭菜還願∕228返厝作墓∕239回到童夢的故地∕252結尾∕264附錄∕265移民作家李秀 致力推廣台灣∕266李秀簽書:《井月澎湖》讓我移民∕268
自序
只為尋找井底那片月光
父母少年時,正是臺灣被殖民的年代,流離困苦寫照每一個澎湖人的生命,掙扎求生是臺灣子民的課題。疲憊雙目,曾見證馬關條約的後遺。冷暖的生命,創傷的心靈,雖曾驚痛於時難的殘敗,但仍不免有刻骨銘心的傳承,而閃出幾許的柔光。
澎湖對現今少年人來說,只是戲水弄潮樂園,待東北季風來臨,又是一片沉寂;在經濟架構上,它只是人口外流的離島;從歷史探尋,它更是西班牙、荷蘭、日本、國民黨政府的化外之島;而我對澎湖的思考,則是從孺慕親情而來的。
澎湖子孫,對根探溯,是無可迴避的主題。基於和文字結緣,做為企圖記錄澎湖人文的我,入侵事件只是一個源起,在這之中突顯出來的是人,是對人性中一切隱秘的剖示和審現。
大之於國邦的衝突,小之於家族兄弟的糾葛,均脫離不了人性的環結。
在歐洲殖民主義尚未偏於乖張之時,歐洲人寫歐洲以外文化,多半以遊記或風土人物誌傳述,如馬可波羅的《中國遊記》通篇充滿欣羨和驚奇;到十九世紀末至廿世紀初,歐洲作家則喜歡以「野蠻對文明」自以為文明人的二分法看待歐洲以外的異質文化;可是廿世紀中期以後,他們開始承認一旦褪去了文明外衣,卸下了白人統治者面具,剩下來的根本僅是人性,而非種族的問題了。
就多族群的臺灣來說,作者勢必從融合出發觀照斯土斯民。融合的過程難免發生對峙、衝突,當恩怨成為彼此共同的歷史經驗時,本土文化無法切割的主體,自然而然就呈現了。
澎湖在臺灣主體性凝聚、蛻動、移位的歷史進程中,從開臺主體退居為以臺灣為主體之下的邊陲。黑水淵深渡過多少移民,滄波興伏間,歷代的來路漸形湮滅不清;荒村棄島,老叟瘦嫗,是要瀕臨歷史的遺忘,還是要從現實重新加深記憶?
於是以思慕溯歸的情懷,完成這部十萬字的《井月澎湖》,從日本入侵開始作為小說背景,傳遞兩個澎湖家族的生活歷史。
歷史事件,雖是過去,但傳到某一時代也是當世的先驗知識,當代對於歷史的見解各有不同的觀點。就大中國一統的立場看施琅與鄭成功,其二者的殺父個人恩怨,無礙於臺灣一統於中國,他們都是擴張中國封疆領土的英雄。但就臺灣主體的立場看,施琅是統派,鄭成功據臺抗清,不正是十足的兩個中國的獨臺傾向?
文學一牽涉歷史,往往陷入歷史迷陣,遭遇有史無文的窘境,這部小說雖從歷史沿起,但也儘量回歸生活縮影,人性彰顯而設身處地化做那時代的人。攀坡臨海,搜集史料,即使一句小小諺語,也求證多方,咀嚼再三,有時亦請陳燕參與推敲。只是創作過程「對話」曾是困擾工事,如果要求自然,那麼重現當時真實語言是不可避免,況且國民黨語言政策推行所謂的「國語」,更不是他們熟悉的語法,像厚話(多嘴)、話屎(流言)、無事使(無價值)、拖屎連(辛苦累人)、創治(惡作劇)、凍霜(吝嗇)……等等,若不使用當時當地語,實難傳神,可是大量使用當時當地語又怕引起隔閡,造成時空限制。如何捏拿得宜,還真要下一番功夫。事實上,澎湖語某些話很文言,好比稱你為「汝」,討一些東西為「討寡物件」……謹慎推敲之際,文字奧妙盡在其中,這也算孤燈夜思中的一項樂趣吧!
將近四個寒暑,《井月澎湖》才完稿。此刻澎湖已不再是抽象名詞,而是具體感受到那一長串的顛沛,我的血緣如斯真實地過活在彼口歷史井月之中。井水如斯冰冷,日月照樣運轉,一井水一世人。小說中人物依舊踏著先祖腳印繼續前進,他們的子孫或許各自忙碌自己的生命旅程,無暇顧及先人的足跡起源。一代傳一代,生命似乎不斷在重覆,是悲是喜,都已不在話下了。也許歷史很容易學,學不來的是歷史的真確。
不管如何,努力經營的這些篇章,不僅僅是愛情、親情,應該還有社會型態的轉變以及斯民對斯土的關愛。但願這把關愛種子,根植於西仔埔頂與天人菊同生吹拂,伴隨低度污染的海岸線,守候著這六十四個島嶼,像珍珠鑲映臺灣海峽之中閃閃發光。
感謝背後搜集資料的人讓我得心應用、王家祥先生能在臺灣時報寶貴篇幅給予連載,以及臺灣文藝的精彩選摘。完稿書序時,緬懷「母土」在跨越世紀之際是否能重新伸展盈涵的旨向?井水中那片照映過母祖的月光,是否也被我孺慕的眸光尋映到了?
此書於一九九六年在臺灣以華文出版,曾獲吳濁流文學獎、高雄市文藝獎。二○○二年以作家之名移居加拿大,為紀念 先父母與台、澎被日本殖民的苦難時代,更想讓較多族群英文人士瞭解故鄉臺灣、澎湖,特將這本歷史小說翻成英文,並於二○一一年在美國 Xlibris 出版“Penghu Moon in the Well”。
華文版已無庫存,「晨星出版社」新版以饗讀者。新版將和英文版相同加入年代,使具歷史真實;書中「對話」將修改更附「台語」味。另外,英文版自序和加拿大作家 Ba rba r aLadouceur 的評介,一併收入其中,以及配合馬公蘇崑雄市長二○一二年美名運動將「馬公」改名為「媽宮」。但願此版更趨完整和可讀性,以不負讀者的期望和厚愛。
李秀
序幕一九九六年夏天船離開高雄港將近三個鐘頭,甲板上蓮子的頭髮迎風披散,強勁的千島海流在澎湖水域的臺灣海峽形成一股黑水溝。貿易風向決定海水的顏色,海面魚鱗斑紋渦流連連,船舷在起伏晃盪中破浪挺進。澎湖人欲往臺灣討生活,在尚未面對千迴百折的風霜之前,首先要歷經黑水溝險惡的試煉。就像昔時帆船一入渦流疊波中,船舵將失去控制,漂流晃盪不知所往。如再遇颱風、暴潮、颶風交相侵襲,行駛在這茫茫海峽上的人命和船舶,就不僅僅是海水變色而已了。蓮子遙望來回穿梭臺灣海峽的點點船隻,心胸隨著澎湃的浪濤,湧動著祖先們自年幼即口耳相傳的鄉里情事,那些悲歡、恩怨,不論直接或間接的深藏在多年來的記憶之中,此刻沈緬於返鄉的情愫裡,禁不住的濕透臉頰,分不清是海水或淚水,在那遙遠的年代,伊彷彿清楚地聽到祥嫂急切的在呼喚著囝兒「山仔」的聲音……Chapter1 井月(1894-1922)1-1火煲生活一九○九年秋天「山仔!去後頂厝討寡人無愛的魚鰓、魚鱗、魚肚。」撿回別人的丟棄物,他們視之為珍品。有腥味調配,霉氣薰人的爛薯籤便不致那麼難嚥了。聽到娘的吩咐,子山擱下手邊牛糞塊,手腳伶俐的持著破舊烏黑的罐子,跑去大人宰魚的地方。通常都能順利撿到,這一天是來遲一步?或無視日頭赤焰焰下一個瘦弱孩童渴盼的意願?他們已把取下的魚渣,統統掃入火煲① 了。子山滿臉通紅,急急衝返去,氣喘喘嗚咽訴說著。做娘的安慰道:「無要緊!洗洗就好了,去撿返來矣!」伊實在不情願,血淋淋、濕漉漉的軟物件,都已丟進亂七八糟的垃圾中,如何撿啊?抬頭觸及娘鼓勵的眼神,伊只好又抓起瓶罐,走向那塊腥氣沖天的所在。「子山!歹撿啦,等一下阿伯提一尾予汝了。」正當伊頭栽入火煲努力尋找時,身後傳來慈善聲調,烏暗的心頭即刻轉為晴朗,伊感激的仰望著冬伯仔,歡喜的展開著眉頭,然後乖乖坐在厝角等候。伊有點迫不及待想飛速告訴娘,咱有真正的魚吃了。從阿伯粗壯的手中將魚小心翼翼接過來貼在胸前,三步併兩步,想用奔的,又驚魚摔落來。心口砰砰響,尚未到厝,即興奮喊著娘!娘!「恁娘去後山埔撿土豆,叫汝趕緊去。」聽了隔壁阿婆的話,伊抓起籃子,往北邊山丘跑去。遠遠望到娘匍著身軀認真翻找土豆,風真大,伊使盡全身奶力,向娘的方面叫著:「咱娘!厝裡有一尾魚哦!」隨後伊發現一簇死藤,收成的人看到地面無莖葉,就無在此處下耙。伊用力拔掉枯藤,小屁股趴跌在土溝,白仁仁的土豆即刻現眼出來。伊驚喜的將視線投向娘,然後放心的想把它剝開,但硬得他手指酸痛,將泥土撥掉,放入嘴裡用後牙一咬,嗶剝開了,生生澀澀也有甜味,嚐過後,挖起來有勁多了。「即馬才來,日頭攏欲落海了。」娘發現伊,隨即一揮手,伊順勢擦了一下鼻涕,「咻」的奔了過去。「娘!阿冬伯仔予咱一尾魚仔。」興沖沖又提起,滿以為娘會歡喜,卻見娘淚光閃爍,頭頓了一陣才說:「好好醃起來,予汝慢慢仔配蕃薯籤。」伊頻頻吞口水,好希望現在就返去。但望著娘蒼白的唇,伊怯怯的講:「咱按呢撿,土豆園阿伯敢會講話?」「厚話!」② 娘即刻叱責過來,見伊驚惶款樣,隨即緩緩說道:「無撿出來,以後嘛會發芽,糟蹋物件。」今日收成不佳,娘的籃子只有一小撮,最近土豆伯較精明,挖得真徹底。天昏地暗,遠處漁船燭光已亮,伊再度感到肚餓難挨,懇求娘收工返厝。凌厲海風,掃盪餓腹的身軀,有如曠野裡的菊,隨風顫搖。循著小山路,母子躓躓頓頓落來,走到巷底,娘叫伊先返去,鍋底尚有一碗蕃薯籤,娘去義叔仔厝,辦了事即返來。娘腳步沉沉踏入厝內,僅追問有燒香拜拜無?隨後僅喝幾口番薯湯就躺在眠床,伊憂心忡忡凝望著老母。「明仔載愛坐早班的船到媽宮③ 。」娘講話聲氣無力。「做啥?去赫遠。」差一點又掉下眼淚。生這大漢,娘從未離開過,除去後山撿土豆、撿柴或到前海抓螺螄外,攏在就近隨時可以見到娘熟悉的身影。但是去媽宮還要坐兩點鐘的船,看!風浪那麼大,娘的小腳,如何走遠路,想到此,大滴目屎滾滾流落來。
 神之雫 最終章~Mariage~(17)
神之雫 最終章~Mariage~(17)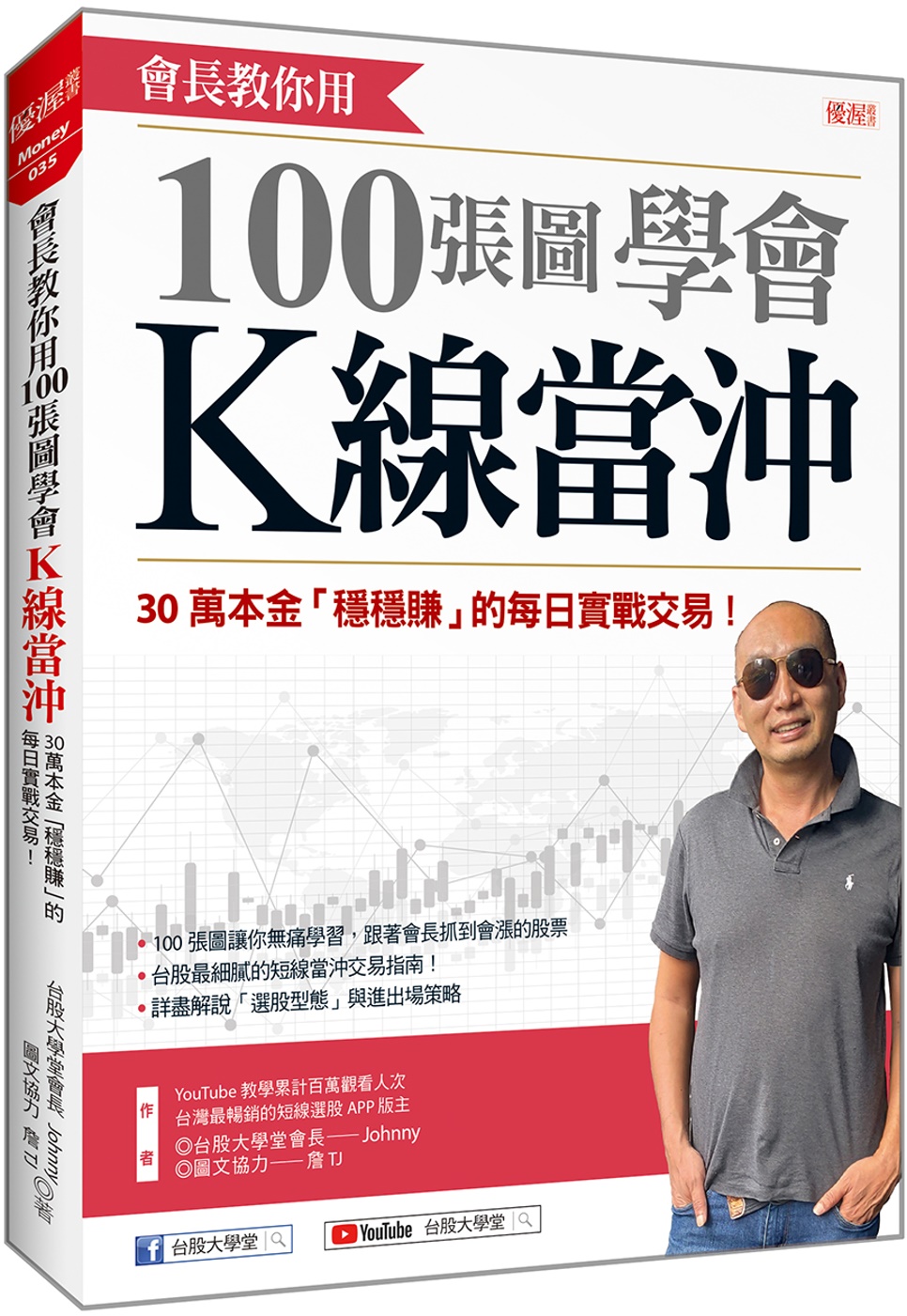 會長教你用 100張圖學會K線當沖...
會長教你用 100張圖學會K線當沖... 完美咖啡的細節:從原豆履歷、杯測口...
完美咖啡的細節:從原豆履歷、杯測口... 台指當沖交易秘訣:操盤手之路
台指當沖交易秘訣:操盤手之路 神之雫 最終章~Mariage~(18)
神之雫 最終章~Mariage~(18) 神之雫 最終章~Mariage~(16)
神之雫 最終章~Mariage~(16)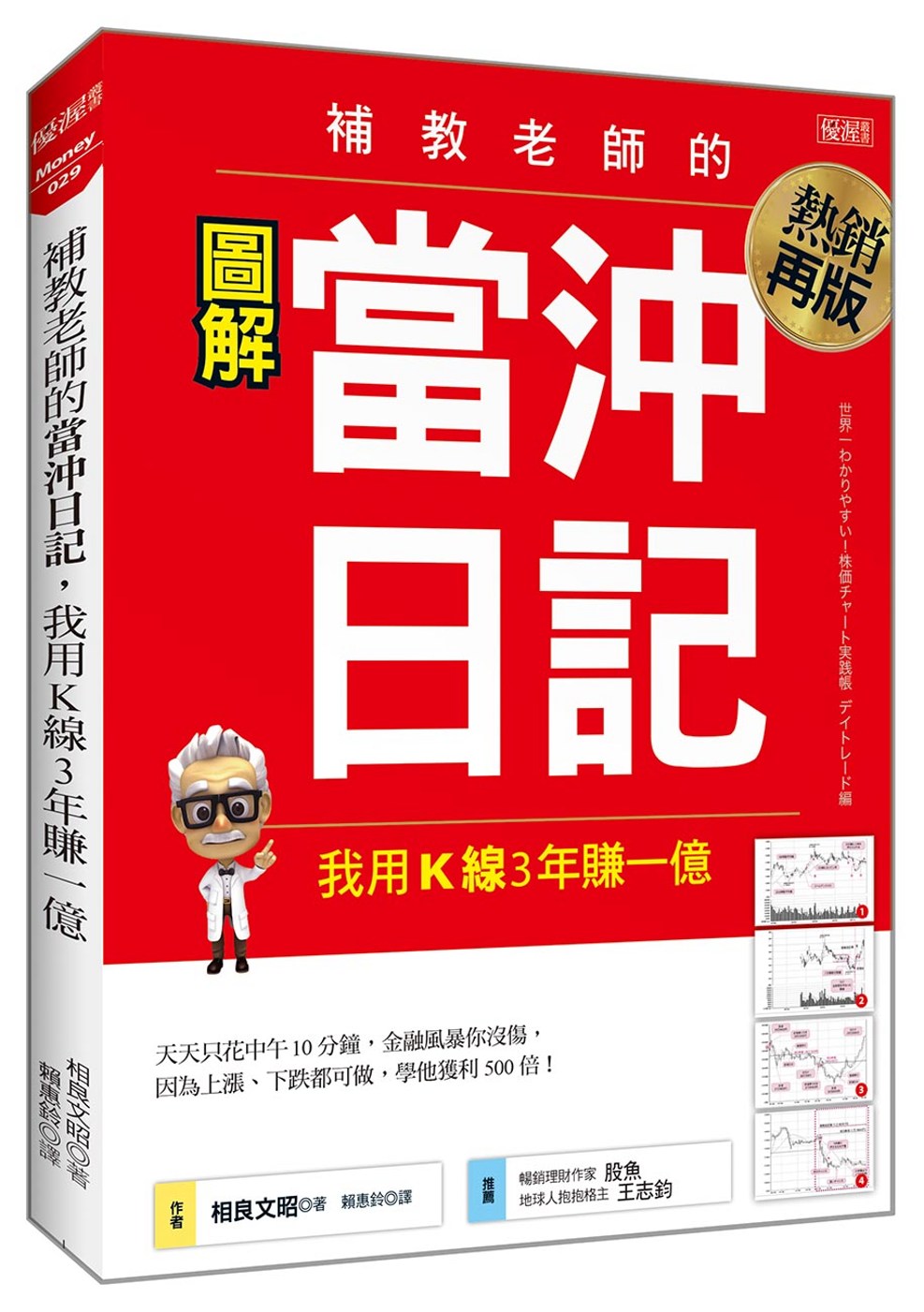 補教老師的當沖日記 我用K線3年賺...
補教老師的當沖日記 我用K線3年賺... 專業當沖原理:選股原則、買賣策略、...
專業當沖原理:選股原則、買賣策略、...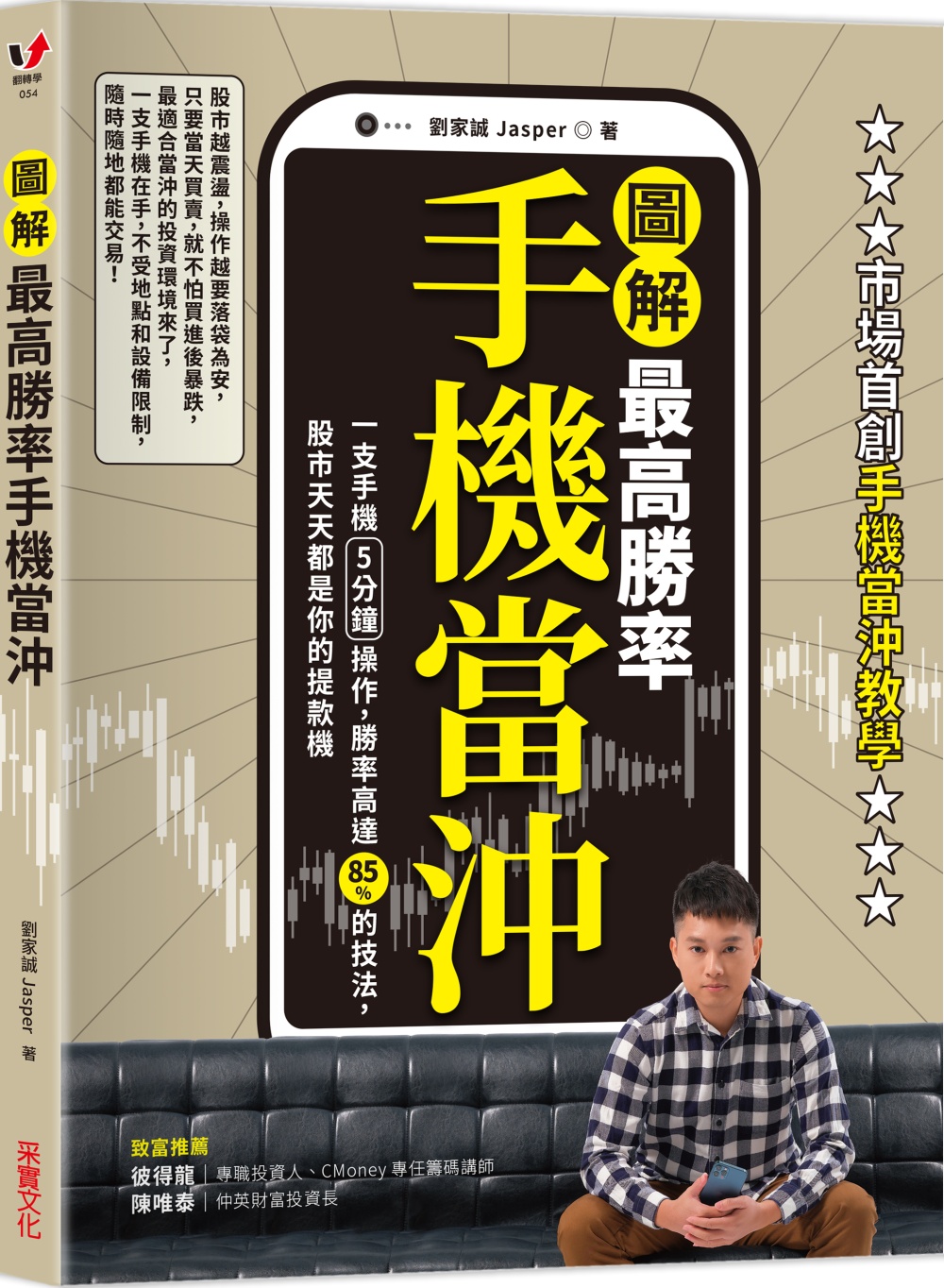 【圖解】最高勝率手機當沖:一支手機...
【圖解】最高勝率手機當沖:一支手機... 世界的浪浪在找家:流浪動物考察與關懷手記
世界的浪浪在找家:流浪動物考察與關懷手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