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奏:香港流行音樂聲像的全球流動 | 運動資訊第一站 - 2024年1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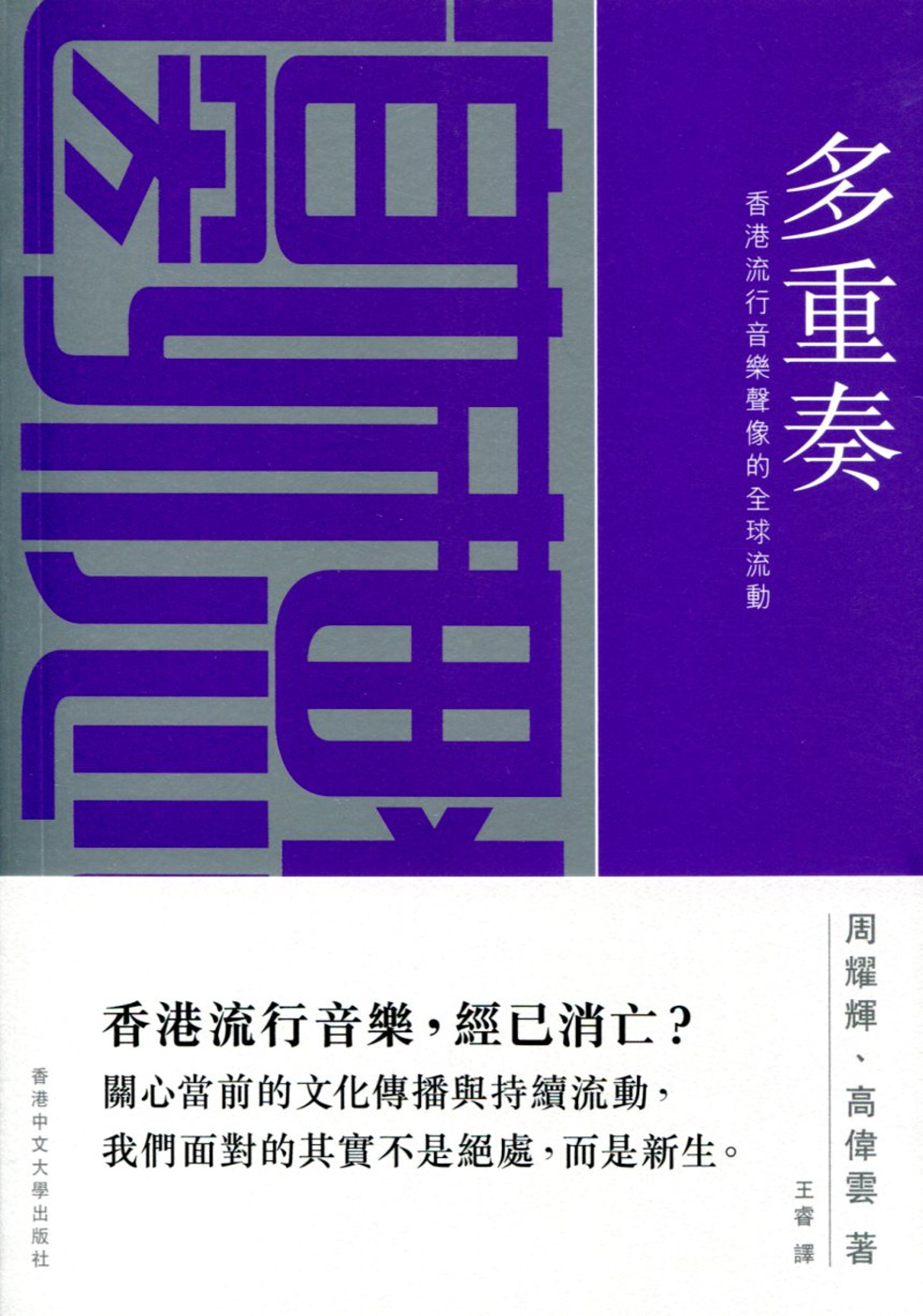
多重奏:香港流行音樂聲像的全球流動
本書橫跨香港過去四十年歷史,以流行音樂為脈絡,嘗試書寫關於身份、記憶、語言和政治的紀錄;以本土特殊性為起點,探討華語流行音樂領域究竟正在發生甚麼。作者之一周耀輝是從事流行音樂20多年的學者。兩位作者從歌詞書寫、視像製造到粉絲文化、唱片公司、表演場所等流行音樂產業的場域切入,逐步展現和分析香港流行音樂生產、消費和流通各環節。
名人推薦
本書聚焦香港流行音樂,把它看作跨越本土,乃至於全球網絡流動的一部分,借此挑撥一些已經固化的名詞,在我們需要面對以至抗衡日漸令人窒息的「中國崛起」之時,尤為重要。──洪美恩,澳洲西雪梨大學文化研究教授
作者對香港流行曲有深入認識,更具紮實的理論基礎,字裏行間又處處流露對香港流行曲的戀戀深情。本書實屬對香港文化、流行音樂、文化研究以至區域研究感興趣者必讀之選。──朱耀偉,香港大學現代語言及文化學院香港研究課程主任
本書帶著局內的懇切與神經,也有局外的淡定和風景。可能我們要退後幾步,與這困局保持一段距離才能看清楚,究竟這個流行音樂工業的確步進夕陽,還是這個城市會再見黎明。──黃耀明,香港音樂人
兩位作者提出鮮活的證據、集體的回憶、另辟蹊徑的論述和自己的故事,反駁「粵語流行曲已死」的說法,同時將中國音樂及粵語流行曲重置於全球化、中國化與重新國家化的交叉口。──馮應謙,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
作者簡介
周耀輝
著文集有《假如我們甚麼都不怕》、《紙上染了藍》。2011年獲阿姆斯特丹大學傳媒學院博士學位,回港任職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助理教授。近年亦參與舞台及視覺藝術創作。
高偉雲(Jeroen de Kloet)
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全球化研究中心總監及教授,研究方向偏重(東亞地區)文化全球化。其著作包括《打口中國:全球化、城市青年和流行音樂》、《景像與城:中國城市化的藝術與流行文化》(與 Lena Scheen 合編)。
譯者簡介
王睿
香港中文大學文學碩士,目前任職於香港大學。
導言 ix
致謝 xxi
圖片說明 xxiii
第一章
人傳的龍:歌詞與中國性的周旋 3
第二章
全球音樂,本地生產:荷蘭、香港粉絲的比較研究 37
第三章
風往哪裏吹:香港中國風音樂錄影帶中的中國性 63
第四章
搭建記憶:香港流行音樂場地 87
第五章
追蹤朱蘭亭:音樂、渴望,以及中國性的跨國策略 109
參考書目 133
索引 147
導言
這個城市不算是一個中轉站。它一直是、或許將來也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港口──一個出入口,一個徘徊於中間的點。[香港的主觀性] 並不是靠自戀而成就的,而是一種構建在不斷拉鋸狀態的主觀性,這種拉鋸發生在殖民主義、國家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突變與重組中。(Abbas 1997: 11)
或許如今的目標不是發現自我,而是拒絕自我。我們必須想像並塑造一個自己,去擺脫這種政治上兩難的局面,即現代權力結構的個性化與一統化在同時間發生。(Foucault [1982] 2000: 336)
聲音的消失
「即使香港流行音樂還沒有消亡,也時日無多了。」
你問每一個見證過香港樂壇盛世的人,大概都會聽到類似的感嘆。他們大多會帶著一種自豪而傷感的情緒再補充說:那個時代多麼輝煌,那個時代產生過多少巨星、多少金曲,那個時代……的確,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是流行音樂的重要輸出地,影響力無遠弗屆。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香港流行音樂是以本土語言「粵語」來演繹的,就是我們常說的「粵語流行曲」,它佔據全球華語金曲流行榜,堪稱「華人的酷聲音」(Chu 2007)。
事到如今,在香港和華人社區的歌唱比賽中,選手大多會選唱台灣歌星的國語歌。香港歌手漸漸將事業(市場)重心轉向中國大陸,相應地,網絡上和唱片鋪中「香港歌手」份額日益縮水。資深粵語詞人黃霑在他的博士論文中明確指出,1997年是香港粵語流行曲時代的終結。那一年,也是香港主權移交中國的一年(黃霑 2003)。這種說法亦得到數據的支持——1995年,粵語流行音樂銷售額為港幣18億5,300萬;三年後的1998年,已經降到9億1,600萬(黃霑2003:169)。一般認為,經濟不景氣、過度商業化以及免費音樂共享技術的發展,導致了香港流行音樂的消亡。2003年,香港兩位本土巨星張國榮和梅艷芳相繼離世,恰似為香港流行音樂敲響了喪鐘。
在大中華範圍內,香港的市場和明星正在萎縮,這是事實。
然而,無論這種說法多有說服力,我們還是試圖提出異議,試圖抽絲剝繭,對它做出補充。本書是從不同方面解讀流行音樂,特別是香港流行音樂的結集。事實上,我們更傾向於用「香港流行音樂」而非「粵語流行曲」這個詞,用「產地」而非「語言」來界定音樂的類別。受所謂「中國崛起論」的影響,學術界的研究越來越多著眼於中國,因此本書更直接的目的,就是為香港在流行音樂研究領域爭取更大的空間。或者說,我們試圖探討及改變的,不僅是正在邊緣化的香港流行音樂,也是日益邊緣化的香港流行音樂研究本身。(關於香港流行音樂消亡的討論,見本書第四章〈搭建記憶:香港流行音樂場地〉。)
以相關著作為例。近十年來,有三部以華語流行音樂為主題的英文專著面世。《打口中國》(China with a Cut)主要探討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北京搖滾樂,其作者 Jeroen de Kloet(高偉雲)也是本書的作者之一。Nimrod Baranovitch撰寫的《中國新聲》(China’s New Voices)同樣以中國大陸為著眼點,重點討論上世紀八十年代至千禧年間的民族和性別問題。Marc L. Moscowitz 的著作和我們的議題較為接近,他在《中國流行音樂的文化意蘊》(Cries of Joy, Songs of Sorrow)一書中,為讀者闡釋了台灣流行音樂如何成為台灣和大陸(尤其是大陸)相當強勢的流行文化,因此全書以台灣國語流行曲為焦點,亦涉及音樂的流動。和以上研究不同的是,本書並沒有放大香港的特殊性,而只是以它為起點,來探討華語流行音樂領域究竟正在發生甚麼,希望藉此理解香港及其流行文化如何交織於中、港、台,以至全球的跨國文化網絡,這當中融匯著人、聲音、影像、物件、意識形態,包括方興未艾的「中國性」。
將香港視為全球文化流動的一個交匯點,也是本書區別於其他中文類香港流行音樂研究之處。本地學者朱耀偉(參與)撰寫了六本關於香港流行音樂的中文著作(朱耀偉 1998, 2000, 2001, 2004;黃志華、朱耀偉、梁偉詩2010;朱耀偉、梁偉詩 2011)。這一系列著作紮根於中國文學研究,或以歌詞、或以香港流行音樂史上某特殊時期,作為文獻收集與分析的基礎。其他著作亦多從文獻紀錄的角度出發,構建本地流行音樂產業起源及發展的歷史脈絡,大致呼應著香港流行音樂已死的論斷(黃志華 2006;黃志淙 2007)。本書參考了這些珍貴的研究成果。不同的是,我們將香港和本地流行音樂置於流動之中觀察,視野超越歌詞的界限,關注流行音樂的多樣性,並以此與悲觀的衰落及消亡論相抗衡。如之前所說,我們希望提供一種不同的解讀,最終重寫香港流行音樂史。用本書有關中國風一章裏的話說,說到底,華語和香港流行音樂的歷史尚待書寫(詳見第三章〈風往哪裏吹:香港中國風音樂錄影帶中的中國性〉)。同時,我們也希望站近區域研究多一點,來反思流行音樂研究。
本書在撰寫時,「中國崛起論」正盛行。受經濟發展的影響,大量研究中國的著作問世,而這裏的「中國」一般是指中國大陸。在全球資本主義背景下,中國經濟崛起,針對中國文化的研究出現井噴,這兩者之間有潛在的微妙聯繫。當今社會,文化已成為資本全球傳播的潤滑劑。如Lash和Lury所言:「文化無所不在,它從上層建築中滲出,影響並控制著基礎建設。……在全球文化產業中,生產和消費就是構建差異的過程。」(Lash and Lury 2007: 4–5)正當北京漸被視為中國崛起的中心,而香港卻由於一直以來所處的東西文化中間位置,使它有可能質疑所謂「中國文化」的重要性(E. Ma 2012)。它既不算是一座中國城市,也不是一座西方城市,正是這種文化上的不確定,有助於我們審視文化在當今全球文化產業中扮演的角色。香港的文化身份註定不完整也不純粹,這更讓我們反思在日漸全球化的時代中,地方、聲音、文化之間的聯繫。
梁學思認為:「政治上不能獨立,香港只能曖昧地表現自己的不同,只能以暗流湧動的形式被察覺,試圖打破水面的平靜。」(H. Leung 2008: 5)也正是這種不確定,使香港非常適合解構文化而非研究文化,質疑中國性而非應和中國性。中國藝術家艾未未也同樣質疑中國文化,以至中國文化平穩過渡為資本的重要性:「所有信仰都會問:你是誰?你認為你是誰?你想成為怎樣的人?或者說,是甚麼讓你相信你會成為那樣的人?可這樣的論述究竟有甚麼基礎?其實我們討論的不外乎是:過去發生了甚麼?現在正在發生些甚麼?將來會發生甚麼?」1本書嘗試進一步探討這些問題,因此我們的分析並沒有過多著墨於香港流行音樂的獨特性,而是著重於香港在全球的聲音、影像及個體流動當中扮演的角色。第一個簡單、基本卻迫切的問題是:當今的全球文化產業,怎麼了?
正在發生甚麼?
本書的論證不僅建立在理論分析的基礎上,也是我們(和其他同業)作為香港流行文化生產者和消費者的經驗之談。本書的作者之一周耀輝從事這一行二十多年,他所感受到的不只是悲觀、無助、掙扎,還有靈活的周旋,求生求變的生命力,但求生產好音樂。如果我們用心聆聽,聽到的絕不止於唱片銷量下降、本土巨星消失這些負面信息。簡而言之,我們的在地經驗讓我們不可能將香港流行音樂看作一個已經消亡的產業。如果我們拿經濟效益(也就是音樂產業主導的指標)與往日黃金歲月相比,情況的確不樂觀。但當我們將關注點轉移到當前持續的文化傳播與流動,所面對的就不是絕處,而是新生。吸引我們的正是文化生產者、產品、場地和消費者以充滿生命力的方式,在城市、國家或任何所謂的本土之中,參與製作音樂,參與書寫音樂史。坦白說,本書很大程度上是我們過去數十年對香港流行音樂情感投入的結晶。借用一句香港話,就是我們不想、也不能把香港流行音樂「睇死」。
Abbas在他很有影響力的《香港:文化與消失的政治》(Hong Kong: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一書中,力證了在 1997年政權移交中國、香港面臨重新中國化的節點上,這座城市的文化與身份是怎樣置之死地而後生的(Abbas 1997)。然而,後殖民地的身份可能永遠都在變化。用Abbas的話說,它不會以一種穩定的表徵出現,或形成另一種穩定的身份,它必須學會擁抱消失,改寫消失,最終超越消失。他認為儘管香港這座城市的流行音樂及流行文化都在九七後蒙上陰影,但或許也因為這個原因,香港才擁有能重塑自身文化和身份的韌力和彈性(1997: 15)。本書以實證研究肯定了他的看法。而我們必須指出,既然說是重塑,就是不停不斷的、無休無止的,因此也難以塑造出固定不變的香港身份。某種程度來說,Abbas可能誇大了九七的重要性,尤其是他認為香港在走向衰亡之時才開始構建身份認同,這一點有待斟酌。事實上,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粵語流行曲興起,甚至更早的粵劇,都顯示香港一直在積極構建文化身份,而這個身份在(後)殖民的背景下,註定是混雜且多變的。
因此,本書關乎時間也關乎空間,研究橫跨香港過去四十年的歷史:從七十年代本土身份出現,八十、九十年代中英談判至最終主權移交帶來種種震盪,一直到千禧年後香港新領導層與北京及大中華地區的調整磨合。各章節以流行音樂為脈絡,嘗試書寫關於香港記憶、身份、語言和政治的紀錄。具體來說,我們從香港流行音樂發軔之初寫起(大概四十多年前吧),這座殖民地開始搭建自己的流行音樂表演場地,本地音樂人也開始以母語(即廣東話)進行創作,其中最著名的應該是許冠傑了。他們不但開創了本地流行音樂傳統,也構建了本土身份。其後二十年,香港流行樂壇持續輸出影響全球的本土巨星,這便是四大天王、兩大天后的時代了。與此同時,香港風雲變幻,1997年政權交接帶來的變動迫在眉睫;1989年北京學生遊行遭到暴力鎮壓,香港人難以繼續一貫的政治冷感。在這個重新中國化的進程中,我們將香港本土的反應寫入流行音樂中。事實上,香港很快就意識到它和中國大陸的融合不只是政治的,更是經濟和文化的。我們看到,大陸市場日益重要,普通話成為主導,一如本文開首所言,大陸和香港的聽眾對台灣流行音樂和歌星越來越趨之若鶩,香港本土流行音樂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關於台灣歌星崛起的深入分析,見Moskowitz 2010)。今時今日,不管是香港,還是香港的流行音樂,都不可能再依仗其輸出優勢及曾經的中心地位,而必須在錯綜複雜的呼應、聯繫與流動中,重新找尋自己的位置。
需要補充的是,我們將本土流行音樂置於跨區域流動的背景下研究,當中的關懷和政治不但關乎所謂本土的製作,也關乎這些製作在本土以外產生的漣漪和影響。大抵在當前歐洲狹隘地方主義的陰影下,我們非常懷疑以本土作為主體或政治推動的可能。我們希望能行前一步,不止將香港這個個案補充到流行音樂研究中,還希望能藉此機會在流行音樂研究、文化研究及區域研究之間架起橋樑。前兩類研究偏重英美,後者又往往過於東方主義,以既定的國族界線來論斷當地文化的所謂獨特性,令「西方」以外的音樂人經常背負地理政治包袱,覺得聽眾期望自己的音樂與本土有密切聯繫。(當然,我們必須強調,所謂「西方」是和已經充分建構的「東方」相對的二元概念,同樣亟待解構。)換句話說,我們不想總是將華語歌曲貼上「中國性」的標籤,而是將其視為複雜的全球網絡(包含影像、媒體報道、網站、歌手、製作人、詞曲作者、音樂產業等)的一部分。這種從本土到全球、從個體到相互關聯的發展與轉變,需要 Tom Solomon(2009)所謂「動態人物記錄」的支撐,當中涉及多個場所和多種類型的參與。當然,儘管地域常常和狹隘的地方主義、國家主義相聯繫,但我們也無意否定地域的重要。事實上,我們對荷蘭和香港粉絲的比較研究(詳見第二章〈全球音樂,本地生產:荷蘭、香港粉絲的比較研究〉)也顯示,在音樂消費階段,地理位置很重要。第四章便描寫了實實在在的音樂場地,是如何搭建起香港的情感記憶。不過,把握住音樂跨國界流動的複雜性,我們相信有更多的故事可以說。本書要說的,就是這些故事。
我們對流行音樂研究的理解出現變化,其實也是對區域及文化研究作出回應。我們的研究表明,以明確而固定的地理界限來劃分地域,隨著文化流動日漸頻繁,顯然存在不足。具體來說,書中所說的「香港」一直都是和大陸、台灣及世界相關聯的概念,將香港流行音樂僅僅放在香港的背景下討論不但不容易,也不可能。其實,不只是香港,任何地區的流行音樂研究都是如此。我們認為,流行音樂研究必須跳出英美主導的局面,不管實證的焦點還是理論的關注,都要去領土化,才能克服重複自身的危險。
如果區域研究依然慣於將地理上的劃分凌駕於文化滲透之上,或硬要脫離港、台流行音樂來研究中國流行音樂,恕我們不能苟同。在瞭解流行音樂如何在全球化時代流動之後,我們認為應避免將香港及中國流行音樂視為兩個不同的研究領域,而要把它們看成有多重密切聯繫,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整體。這不但必要,也更有效(參閱Groenewegen 2011)。當我們將本地流行音樂置於跨區域的流動中時,不可避免地會對區域劃分提出質疑,要求打破並重新審視這種藩籬。例如,還有哪些勾劃音樂地圖的可能?音樂的流動又怎樣重新釐定政治、文化和社會界限?
我們對於文化研究的回應,則分為三個層面。首先,如之前所說,書中所研究的香港流行音樂個案,主要來自我們對香港及中國流行音樂的觀察。從這點來看,可說是響應了 Angela McRobbie(1997)對文化研究提出的「3E」呼籲(empirical, ethnographic, experiential;即實證、人本、經驗)。Michael Pickering 闡釋說:「如果我們能讓文化研究的調查與分析多一點對證據的敏感,少一點理論上的自以為是;多一些以參與者為導向,少一些對自身知識理論的著緊,我們便能推動這個領域的進步」(2008: 5)。這也是本書努力的方向。其次,本書的考察涵蓋流行音樂研究的多個方面,包括製作、呈現、消費。從這個意義上,本書對文化研究中接收和消費研究的某些偏頗做了補充,它們「似乎假設了消費者是最終決定文化意義的人」(Hesmondhalgh and Baker 2011)。第三,從更廣義的角度來看,本書採用某種文化研究的策略,試圖避免跌入理論主義的陷阱,簡單來說,就是為正在發生的,書寫更好的故事。如 Larry Grossberg 所說:「文化研究試圖去講一些更好的故事,讓人們想像未來有其他(更好的)可能,同時想像有其他(更好的)策略去爭取實現這些可能」(2010: 242)。因此,本書的理論部分兼收並蓄,根據個案研究的需要,提出需要探討的議題和需要介入的辯論。
因此,我們堅持流行音樂研究與區域及文化研究交叉進行。在對全書內容做概述之前,我們先簡單介紹所採用的方法。一如其理論部分,本書所採用的研究方法五花八門,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個大雜燴。我們從自傳開始,輔以文本分析,接著是種種社會科學的定性研究方法,包括訪談、小組討論、參與觀察等,還有一些類似人文學科的方法,如視覺文本分析等;最後,我們追蹤某個個體的跨國歷程,這位研究對象亦同時成了研究的主導。
內容概述
全書以香港流行音樂傳統中一個獨特類型「民族歌曲」開篇。對周耀輝這位文化研究者及文化生產者(填詞人)而言,民族歌曲的力量恰恰在於偏重某種中國性的表演。1980年,他曾唱過一首民族歌曲;2004年,他自己寫了一首。第一章是一個自傳式的書寫,探討在香港中國化的大背景下,作者是怎樣處理在流行歌詞創作中遇到的中國性問題。第二章從構建國家轉到全球流行音樂中如何構建本土。我們把焦點放在兩位本地歌星—香港的黎明和荷蘭的Marco Borsato,以他們的粉絲做比較,結果顯示差異明顯。簡言之,荷蘭的粉絲將Marco 視為一個平凡的人,而香港的粉絲則將黎明塑造成一個非凡的工作者。在全球化理論下,我們認為很有必要將地方性納入歌迷研究的範疇。
第三章對較近期出現的流行音樂現象「中國風」做了考察。全章並非著眼於台灣這個被普遍認為是中國風歌曲的發源地,而是以香港的中國風歌曲及錄影帶作為研究對象。分析顯示,香港的中國風流行曲喚起了中國意識的同時,也從兩方面削弱了中國性─它一方面將中國性變為一種遠觀,一個曖昧的空間,一場永恆的掙扎;另一方面將中國性女性化,為歷史及性別表演留下質疑的空間。香港流行音樂在九七之後被宣告消亡,但同時出現的一系列歌手樂隊復出 / 重聚演唱會,卻像在力挽狂瀾,顯示香港歌星依然重要。在第四章,我們將視線聚焦於音樂的消費階段,從香港音樂場所的歷史著手,分析它們是怎樣在一個看似變幻莫測的城市中,豎起情感的里程碑。尤其是香港體育館(紅館),又是怎樣幫助這座城市和城市中的人跨越時間,搭建自己,憶記自己。
第五章講述了朱蘭亭(後改藝名王詩安)的故事。生長於荷蘭的朱蘭亭,15 歲時獲得2006年阿姆斯特丹華人歌唱比賽冠軍,後來簽約香港華納與台灣華納唱片,甚至移居父母的故鄉上海,為進軍華語流行音樂市場的希望而努力。我們採用Lash和Lury的「追蹤」研究方法,追隨朱蘭亭,觀察到她與唱片公司在語言、音樂與身體上的拉扯;這些拉扯不單是與華納的,歸根究底,更是與中國目前構建與經營希望的種種勢力的拉扯。
與此同時,我們也藉第五章的個案研究,反思當代流行文化研究的方法。換句話說,可以把最後一章看作是對全書的一個方法論註腳。再者,儘管我們的反思來自對香港流行音樂的研究,但我們的呼籲卻關乎更廣闊的流行文化研究。簡言之,我們認為,研究必須建立在把握流行文化與流動、身體、政治和個人關係的基礎上。
注釋
1 艾未未訪談節選,原文見和文朝(2008):〈荒誕中的自我證明:艾未未談798現象〉,載黃銳編:《北京798:再創造的工廠》(四川:四川美術出版社),頁39。
 戰鬥!暴風少女!series2
戰鬥!暴風少女!series2 小奧爾多成長記:女生止步
小奧爾多成長記:女生止步 習慣改變了,頭腦就會變好:東大生教...
習慣改變了,頭腦就會變好:東大生教... 小奧爾多成長記:冒牌貨
小奧爾多成長記:冒牌貨 戰鬥!暴風少女!Series 1
戰鬥!暴風少女!Series 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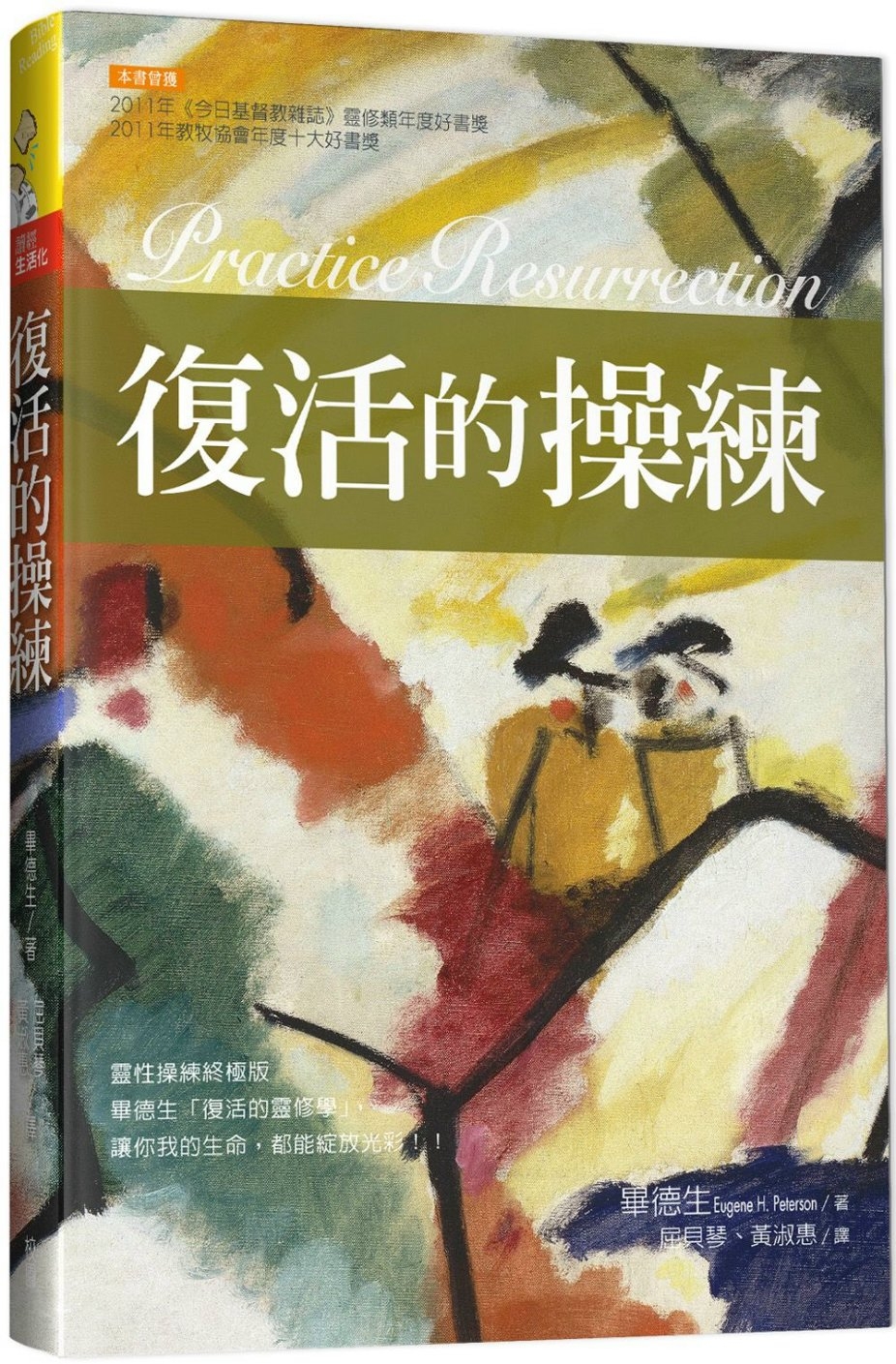 復活的操練
復活的操練 速度、敏捷及反應的運動訓練法-含2...
速度、敏捷及反應的運動訓練法-含2... 核心體能訓練:釋放核心潛能的動作練...
核心體能訓練:釋放核心潛能的動作練... 蟲之歌 06 引夢的旅人
蟲之歌 06 引夢的旅人 女子運動員體能訓練
女子運動員體能訓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