裡面的裡面 | 運動資訊第一站 - 2024年11月

裡面的裡面
金鼎獎推薦優秀新銳小說家重量級長篇著作
揭開不為人知的台共家族故事及白色恐怖時期祕聞
二二八事件時,一位日治時期被判刑最重的前台灣共產黨信仔,在大姊潘笑的幫助下潛藏出逃。他先是奇蹟式地逃過了仄窄閣樓間憲兵的追查,超現實般隱匿在老舊的木條和牆面之間沒被發現,之後他沉默卻有神祕感知能力的大姊繼續安排他搭船逃離,並由外甥阿寬護送。阿寬作為信仔舅舅逃離台灣的共犯,見證其失蹤者,即便後來當他聽聞信仔已亡故,仍裝作不知情。因為作為家屬遺族,是不能承認他們之間是有聯繫的。幸好,阿寬仍有個秘密支持著自己。畢竟這世間唯獨他,依稀看到信仔從助他出逃的破船跳下去的身影。幾回感覺支撐不住時,他總回想此幕,歡快猜想或許信仔一直在逃,逍遙的以另外一種身分度過餘生……
而那夜之後,信仔的空缺,就此影響了許多人的餘生:新寡的大姊潘笑,一世人沉默;獨自扶養女兒們長大並照顧著信的朋友後代們的信仔妻子盆,懷藏祕密並勇敢堅強度過終生;外甥阿寬,幫助他潛逃的見證者,也是與他最相像的、少點靈感卻多些憂鬱的後輩,在他帶領下讀了許多書,卻對知識的力量既敬又懼,以及與他命運平行、遠在滿洲國的二哥仁……
《裡面的裡面》以真實的歷史背景為故事的舞台,埋藏了信仔告別世間的最後幻想,小說並虛構了一位將來能破譯信息的後裔。而這名後裔,將追尋所有被抹去的痕跡、聆聽沉默的聲音、思考那不可思考的事物,最終,虛構起信仔以及他們的故事。朱嘉漢這部長篇匯集了一直以來廣義白色恐怖小說的面向,做了新階段的嘗試。小說時而低吟、時而高歌,以現代文藝語彙雜揉台語文語感,切片敘述著台灣共產黨、日治時期、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滿洲國的起落等等,不論這些元素以往如何各自缺席或沉默,整部小說以立體拼圖的方式做了巧妙連結,故事中的角色在不屬於他們的時代之中,將自身的命運折疊再折疊,藏在裡面的裡面,並遙遠地留待給無緣相識的子孫。
名人推薦
學界、文壇 一致肯定推薦
學界代表 王德威、陳芳明
小說名家 黃崇凱、賴香吟
青年作家 林新惠、洪明道 (依姓氏筆畫順序)
名人推薦
「這部小說,恰巧是行方不明的故事,它開放了去向的可能,但這個去向,可能,終究指向我們自身內部;行方不明的焦慮與思念,在時空之中變生意義。讀著讀著,我知道我走在新的路徑,我樂見,我們的記憶,走到這個境地。」──賴香吟
「《裡面的裡面》可以說是匯總過去廣義白色恐怖小說的機制,做了階段性的集結,展現『事件』在女性、同輩、後代身上施力,並用立體拼圖的方式組合成了長篇小說,具備相當的完整性。小說時而低吟、時而高歌,以現代文藝語彙雜揉台語文語感,回顧思考諸角色的一生並賦予詮釋,使得角色們帶有浪漫英雄色彩。」──洪明道
「《裡面的裡面》和我們身處的台灣——在這塊土地上層疊的記憶、文化、歷史——互為因果。正因台灣的歷史如此交纏繁複,才能孕育出《裡面》這樣一部既虛構又真實的敘事;正因為《裡面》摻雜了歷史事實與小說家的虛構技藝,才讓台灣的歷史與記憶得以被述說,也因為被述說而得以續存。」──林新惠
作者簡介
朱嘉漢
朱嘉漢,1983年生。曾就讀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社會學博士班。現為台北藝術大學兼任講師。寫小說與Essays。著有長篇小說《禮物》、《裡面的裡面》。
第一章 把自己折疊的男人
第二章 他沒有搭上那條船
第三章 寡婦
第四章 方向
第五章 跟蹤與失蹤
第六章 通譯者
第七章 不笑
第八章 焚書
第九章 遠方的信
【推薦跋】追蹤離開的小船,在大船上 ◎洪明道
【評析】裡面的反饋迴路:朱嘉漢的小說系統 ◎林新惠
【附錄】小說家的對話/賴香吟與朱嘉漢通信錄
推薦跋
追蹤離開的小船,在大船上
洪明道
朱嘉漢和我的第一本書在2018年底發表,因為意義上的關聯,被我的出版社企劃視為同一主題的兩種聲道。
儘管在追索的核心有部份重疊,我們的挖掘方式是很不一樣的。如果說是同期出道的話,差別大概有Leo王和流氓阿德那麼大。閱讀朱家漢的《禮物》時,除了感受到「寫作者」這個敘事聲音的高度自覺,也可看見朱嘉漢意圖用語文製造差距,時時反思理論和概念。我卻是隱身文字之後,默認寫作者和讀者的契約,逕自說故事的那種。不得不承認,《禮物》和我所熟悉的小說路數,在光譜可以說是相距甚遠的,我必須耗費極大的精神閱讀《禮物》。
然而,《裡面的裡面》是一本在光譜上靠過來一些的小說,並處理了離當代頗遠的歷史,台灣共產黨領導人潘欽信的故事。這種遠並非時間上的遙遠,而是政治上對左翼思想保持的遠、歷史教育裡對台灣共產黨的遠,再加上現今華語環境距離當時日語、台語的遙遠,使得《裡面的裡面》的企圖令人敬佩。
相迫和相倚
在當今要處理相對遠的台灣歷史,寫作者已經沒有前輩需要在文字裡躲藏的必要。另一方面,台灣研究經歷前人突破禁忌、形成學科,到現在有了一定的成果,在責任和倫理之下,寫作者很難再用「歷史只是詮釋和虛假」來施展幻術,虛構也難以無限上綱。
當代寫作者佔據另一種優勢,是我們可以借用這些積累,在自由的創作條件下變化出不同敘事方式。但同時也面臨挑戰。得想辦法讓作品在滿溢的資訊裡佔有一席注意力,埋下抓人的鉤子。另一個難以繞過的障礙,則是即使在地毯式搜索之後,仍存在的史料、研究的空缺。
對於這樣的空缺,研究者自有迫倚(pik-uá)的方式,需要頂真相迫,嘛愛用心相倚。《毋甘願的電影史》添加了給讀者的糖、實在的乾貨、一切美好的味道,還有做為化學物X的熱忱和眼淚,在非虛構框架下創造出了佳構。
《裡面的裡面》毫不迴避地迎向這樣的空缺,利用小說的方式去迫倚。在相迫的部分,小說九個章節由信仔、阿寬、盆、潘笑等人輪番上場,試圖去逼近更大的全貌。這樣的結構不只達到〈竹藪中〉並陳故事版本讓讀者參與的效果,也展現了「事件」在這些人物身上各自的痕跡。《裡面的裡面》可以說是匯總過去廣義白色恐怖小說的機制,做了階段性的集結,展現「事件」在女性、同輩、後代身上施力,並用立體拼圖的方式組合成了長篇小說,具備相當的完整性。
另外一種小說特長的處理方式,則是心理上的相倚。小說的全知者不時穿越時空和人物站在一起,「你不知道如果選擇切斷關係,會留下多少把柄在他人手上」、「而是某個瞬間賜予你的時刻,將某些你以為失去東西原原本本還給你」。在這些段落,已經預知後來故事的全知者,私密的和面臨抉擇的人物對談,或為這些人物的一生下註解。
這讓我想起巴爾加斯尤薩的《天堂在另一個街角》。在這本交替描述芙蘿拉、高更一生的長篇小說裡,同樣頻頻用「你」來靠近這些時代異端者的心靈。兩相比較下,《裡面的裡面》透露出更多疼惜和謳歌,《天堂在另一個街角》則多了一點距離和懷疑。《裡面的裡面》借用了小說擅長的技術,以現在的心靈去探測過去的心靈,給了一份探測紀錄。
而對信仔來說,天堂也是否在另一個街角?我們現在又距離那個街角多遠?這也是《裡面的裡面》一再提問的。
在《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中,林傳凱反省了口述史的可靠性、敘事生產的脈絡和社會氛圍對當事人敘事時的影響。同樣作為提取記憶的手藝,這些反省也可以做為創作小說的提醒。
不同時代採集的口述史總是有不同版本。由不同受訪者集結起來的口述史,也會組合出不同意義。在《裡面的裡面》的潘欽信,是透過其家屬親族視角組合出來、親暱且為台語聲道的「信仔」,小說從頭到尾並未將「潘欽信」這個歷史學界的、史料上的名字給貼在人物上。
《裡面的裡面》終章掀開了書寫的過程。終章裡的「他」可以作為小說的定位點,也誠實交代了一些限制。「他」的家族經歷集體性遺忘,「他」無可避免的處在語言斷裂後的社會,在教養過程中被隔絕於左翼和人文知識之外。「他」和信仔、讀者和他之間的關係,都可以視為事件的延伸作用之一。
百年後的武勇和廢青
回到小說本身,《裡面的裡面》時而低吟、時而高歌,以現代文藝語彙雜揉台語文語感,回顧思考諸角色的一生並賦予詮釋,使得角色們帶有浪漫英雄色彩。這種做法的另一面,是會讓敘事節奏停滯。
儘管我會期待在用概念統攝之前,有更多個案性的細節和差異,拓印出歷史角落裡人的細碎紋路。不過,這是小說藝術自帶的限制。精雕圖式(pattern)的同時必得壓縮人物,情節也會受牽制,小說家只能盡力走在狹窄的平衡木上。《裡面的裡面》見長之處便在於圖式,無論是結構的對稱、人物之間的互相補充,形塑出做為整體的美感,意義的湧泉也往往在其中迸發。
小說的跳躍處往往是象徵或意義傳達的重點,諸如潘欽信看見血色的基隆海港、阿寬請盆擔任好命婆,幾處時空斷接令我十分震撼。時間尺度的瞬間拉長,能讓我們重新評價小說中運動的失敗。
放在台灣小說的長河裡,《裡面的裡面》帶領我們看見百年前武勇的樣子,王詩琅〈沒落〉正好可以一起閱讀。相對於〈沒落〉裡轉向的耀源,信仔則是下獄的那個。無論下獄或轉向,運動的失敗已然發生,運動者和具連帶關係者往後的生活,都是小說開始說話的地方。
走過歷史的十字路口後,我們已經很難想像要完全突推翻資本主義基礎的社會制度。回頭看這些信奉主義的職業革命家,也許會感到隔閡,但懷抱對另一種社會狀態追索的人,在哪個時代都會有。
《永別書》裡有一段,呂赫若的後代和同學在一番輕鬆地聊天後,說了一句「呂赫若是個真正的才子」。「要是她可以不用說呂赫若是個真正的才子,該有多好」,《永別書》這麼寫。
無論呂赫若或潘欽信,人們都不那麼記得他們。在《裡面的裡面》從幽暗處帶給我們「信仔」的故事。期待潘欽信和信仔之後的調和以及解放,也祝福記憶和意義能繼續生長下去。
評析
裡面的反饋迴路:朱嘉漢的小說系統
林新惠
朱嘉漢新作《裡面的裡面》,以他擅長的歐陸哲學,敘述台灣共產黨員潘欽信及其親屬的生命故事。換句話說,《裡面》可說是以歐陸哲學的語言,講台灣日治至白色恐怖這一時間軸的歷史。如此跨領域、跨文化、跨時空的嘗試,勢必吸引各方評論關注。而在台灣歷史文化的關懷之外,本文希望以哲學理論解析《裡面》,探問小說裡面的裡面,隱藏於深邃內核的敘事機關和思考模式。
這個深藏於內核的機關之一,是反饋迴路(feedback loop)。本文試圖辨識《裡面》作為一個敘事結構,如何以反饋迴路構築而成。如同最小的齒輪(反饋迴路)構成了繁複了時鐘(小說),甚至銘刻外部的時間(小說敘述的時空脈絡)。
反饋迴路意指兩個單位相互構成。經典的例子是M. C. Escher的畫作《繪圖的手》(Drawing Hands)。在這幅畫中,一隻手畫出了另一隻手:構成A手的所有素材(光影、線條、「畫畫」這個行為)都來自B手,而構成B手的所有素材,又是來自它所繪製的A手。一隻手畫出去的東西,最終會回歸到自身,這是回饋(feedback);而回饋的重複發生,就是迴路(loop)。
「回饋」的概念也許讓人想起朱嘉漢的第一本小說《禮物》。該書以牟斯(Marcel Mauss)的禮物論為核心,追索書寫的「給出」與「回返」路徑。小說中四人不停思考如何寫小說,甚至籌組一同研討如何寫小說的讀書會,但是沒有一人真正寫出普遍意義上的小說——沒有一人寫成足夠篇幅、甚至每個短篇都很零碎不成篇、沒有找出版社洽談等等。這是「給出」的過程。這種「給出」在概念上類似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的「耗費」(expenditure):不講求保存、不計較實用性、在時間意義上沒有「未來」這個向度。談了老半天「小說是什麼」卻寫不出一部小說,這種給出看似毫無意義且徒勞無功。然而,朱嘉漢透過《禮物》,描繪了「給出」的回返——也就是《禮物》本身。也就是說,小說敘事者「朱嘉漢」,搜集了小說中四個角色的斷簡殘篇和讀書會的討論過程記錄,最後以小說家朱嘉漢的名義出版了《禮物》。《禮物》的出版,讓小說四人的「給出」得以「回返」:心心念念寫小說的四個人,費心留下「不是小說」的散亂文字,然而這些文字終究由他人之手而成為一本長篇小說。這本長篇小說是他們四人孜孜矻矻給出之後的「回返」。反過來說,聲稱自己只是負責搜集和組織文字的敘事者「朱嘉漢」,卻也透過「給出」搜集和組織的心力,而得到「回返」:出版一本屬於現實意義上的,屬於小說家朱嘉漢的小說。
《禮物》將「反饋」的概念開展成眩惑人的迷宮,而在《裡面》,「反饋」之後還要加上「迴路」。反饋已經夠繁雜了,又加上迴路,看似越講越難,其實正好相反:正因為多了迴路,反而變得簡明透徹。如果《禮物》是見山不是山(把概念講得很玄很難),《裡面》則是見山又是山(將概念化繁為簡,四兩撥千斤)。
在《禮物》,朱嘉漢寫了一個故事,故事關於四個人寫故事的過程;也就是說,《禮物》是「A虛構B虛構C」的過程。 在《裡面》,朱嘉漢虛構潘欽信的故事,而故事內的潘欽信,透過小說最終的書信,虛構了朱嘉漢;也就是說,《裡面》是「A虛構B虛構A虛構B……」的無限迴圈,就像Escher的畫。
我們先從「A(朱嘉漢)虛構B(潘欽信)」開始。潘欽信是確實存在過的人物,但在《裡面》當中,潘欽信毋寧更像被朱嘉漢虛構的角色。必須強調的是,虛構並不意味造假、腦補、無中生有,而是在缺席之上複寫:正因為「歷史人物」潘欽信的史料充滿空白,才使得朱嘉漢可以創造出「小說角色」潘欽信。朱嘉漢既不是原汁原味地呈現潘欽信的史料(例如緊密貼合歷史事實的小說),也不是借潘欽信之名而敘述遠離歷史脈絡之故事(例如《文豪野犬》)。 《裡面》的潘欽信的遭遇,大致對應到史料記載的事件,如與共產黨的糾葛、在二二八事件中的逃亡、被標籤為「失蹤」等等。但是關於潘欽信的內心世界、逃亡的細節、甚至和親人間的關係,都是小說家的虛構。
有趣的是,小說並不隱藏虛構,反而開宗明義就揭露了虛構——這在涉及歷史的小說敘事中尤其少見。《裡面》第一章敘述潘欽信為了躲避國民黨軍官的追蹤,把自己窩進大姊潘笑家裡的閣樓,並且奇蹟似地,在軍官搜索到閣樓時,明明就蹲在警察的褲檔前,卻完全沒被警察發現,因而逃過了被逮捕的命運,最終得以搭船逃亡香港。這個小說中稱為「屎溝巷的奇蹟」,在時間軸線上對應到歷史事實(逃躲國民黨的追捕之後再搭船到香港),但在時間軸線上發生的故事細節,則是小說的虛構(閣樓、在警察褲檔前隱形等等)。在這些故事細節之內,則有更繁複的虛構:潘欽信躲在閣樓中,開展了關於自己人生的,近乎哲學般的辯證和經歷。例如他思考自身存在的意義,建立在絕對的否定之上;他認為自己在歷史的缺席就是屬於他的剩餘價值;或如當他的臉貼著軍官的褲檔,經驗了瀕臨死亡的性愉悅。這種歐洲哲學式的悖論(存有vs否定)、將馬克思思想挪用到生命意義的思索(深陷動盪時代的共產黨員竟如此細緻地思考剩餘價值的意義)、甚至出現了巴塔耶式的小說情節(交纏死亡、痛苦、性愉悅的極限經驗),都非常明顯地告訴讀者:這是朱嘉漢使用自己的哲學知識,填充進「潘欽信」這個歷史人物的軀殼,所構成的小說角色。
這些看似違和的設定,到了最終章卻變得十分合理:原來前八章的故事,都是潘欽信的三姪子阿寬的小說家內孫所做的虛構。這位和潘欽信有著遙遠血緣關係的小說家,因為家族間流傳的軼事、以及遺留下來的稀薄史料,得知潘欽信和他的三姪子阿寬等人的故事。但小說家所做的,不但不是講求真實的考究,反而是看似偏離真實的虛構——小說家在最終章承認自己虛構了潘欽信。然而,弔詭的是,正因為這些故事是虛構的,才讓這些曾經存在於過去時空的人物彼此串連,且直通現代。小說家娓娓道來自己取得歷史材料及虛構所有角色的心路歷程。通靈似地,小說家和所有既是虛構也是實存的人物,透過「虛構」這個行為構築了跨越時空和心智限制的對話及感應。
正因為潘欽信是如此層次上的虛構——一個立基於歷史事實卻摻雜大量後設虛構的存在——才使得全書最終,潘欽信躲在閣樓當中寫給未來小說家的信,得以成立。這正是「B(潘欽信)虛構A(朱嘉漢)」發生之時。《裡面》的最終章最後一節,是潘欽信寫的信,收信者是他所虛構的一個人,因為他需要那個他虛構的人,代替他思考,述說他的故事。而那個被潘欽信虛構的小說家,所說的關於潘欽信的故事、所形構的潘欽信的思考,就這麼銜接回全書的最開頭:也就是前述潘欽信躲在閣樓時,綿延的思緒及驚險的經歷。
最後一章接回第一章。被小說家虛構的潘欽信,虛構了小說家。小說虛構了歷史,歷史也虛構了小說。反饋迴路,於焉構成。
最後,讓我們再回到Escher的畫。
Escher的反饋迴路得以成形,不只在於「手畫手」這個意念而已。Escher的畫,更仔細地說,是手「在紙上」畫手。「在紙上」意味著,「手畫手」這個意念,具體落實在外部脈絡之中(紙張);也意味著,手畫手這個反饋迴路,必須發生在一個環境當中(紙張),才會成立。
《裡面》的反饋迴路亦如是。《裡面》的敘事邏輯,就像「手畫手」一樣,是一種概念;而小說具體涉及的台灣歷史文化,則是承載「手畫手」的紙張。如果說《裡面》是一組反饋迴路系統,那麼台灣歷史文化,就是讓系統得以發生和運行的環境。並且,也是因為系統的運行——也就是《裡面》這本小說以反饋迴路所構成——才讓環境(台灣歷史文化)擁有更豐富繁華的模樣。
「系統」和「環境」的相互共生及辯證,正是德國社會學家魯曼(Niklas Luhmann)所提出的系統理論。如同魯曼所言,「系統透過那些組成它們的元素來進行自我生產,並且再生產那些組成它們的元素」,我們可以把這句話當中的「系統」,替換成「《裡面》」,並把「組成它們的元素」替換成《裡面》中出現的歷史人物和小說家。並且,這個系統(《裡面》)是以因果關聯性上開放的(kausal offen)方式,和環境(台灣歷史文化)產生關聯。也就是說,《裡面》和我們身處的台灣——在這塊土地上層疊的記憶、文化、歷史——互為因果。正因台灣的歷史如此交纏繁複,才能孕育出《裡面》這樣一部既虛構又真實的敘事;正因為《裡面》摻雜了歷史事實與小說家的虛構技藝,才讓台灣的歷史與記憶得以被述說,也因為被述說而得以續存。
朱嘉漢的小說系統,是以小說探問「虛構可以通往何處」。《禮物》是以純粹虛構,彷彿俄羅斯娃娃般通往無盡深處。而《裡面》藉著虛構真實,創造了時空的莫比烏斯環。歷史材料的裡面,是小說家的虛構,小說家虛構的裡面,是對於記憶的塑形。當我們抵達裡面的裡面,抵達這份記憶,卻又蟲洞般地,通往外部,通往我們所處的此時此地。這正是潘欽信最終的信,由遙遠的過去,所傳遞到的彼方。
而我們終將在此時此地閱讀《裡面》,再度掉入敘事迴圈,一如潘欽信將無限循環地走入小說家的故事中。
第一章 把自己折疊的男人 他一直想要拯救的那個人已經被抹去了。 像是將玻璃窗上的半透明污漬、雨水流過後宛若溪川的細痕、鴿子屎,用抹布沾點水輕輕擦掉後的樣子。乾淨得如同因擦拭而留下來痕跡的比他們刻意為之的多。他知道同志們都有徹底的覺悟了:他們將留下的,並不是存活過的痕跡,而是被抹去的痕跡。他的同類們,關係始終游離,充滿了衝突、不信任、背叛與密報。只是在最後,以完美的技術抹拭乾淨,成了共同的命運,雖然無緣知曉,但也不重要了。 他仍有一點點不甘心,想大聲對誰抗議一下。等在面前的,怎會是全然背離他們所願的死。即使他們仍然年輕,但命運使然,他們看待前幾年的革命歲月猶如前世蒼老。 他們等待。死,本該如武士切腹。他,以及他的朋友們,充滿奇想地企盼這種形式的死亡。因其乏味,才有條件在那一切的行動裡,專心地製造死亡。他們在想像中,練習能夠每次都召喚出精確無比的想像畫面與細節。切腹是最無言的死,因為他認為所有的思考或是語言,存在不得不呼應的黑暗。那是人的存在在面對難以承擔的黑暗時的吶喊。切腹這樣無須言語,甚至扼殺言語的死,如此光明。光明得像是直視烈日。 不怕孤獨的他們,卻怕極了孤獨的死。他們暗中交流,以化名與暗號,互相帶著假面打交道時,也許都想過他們是怎樣的以死誓盟。他們的命,如此朝不保夕,不殃及親友已是萬幸的有罪之身(儘管大部分的他們,甚少真正傷害過任何人)。生死互繫,產生一種錯覺:每一回任務的完成,躲過眼線後,都感覺自己的命是被拯救的。於是,與理智不相符地,他一次次投入、以身犯險,皆感到救贖。原來該死的那條命,被上天允諾多延長一些。久了,命感覺是偷來的。直到死亡到臨,才能卸下責任,完成最後的任務了。
 小書痴的下剋上:為了成為圖書管理員...
小書痴的下剋上:為了成為圖書管理員...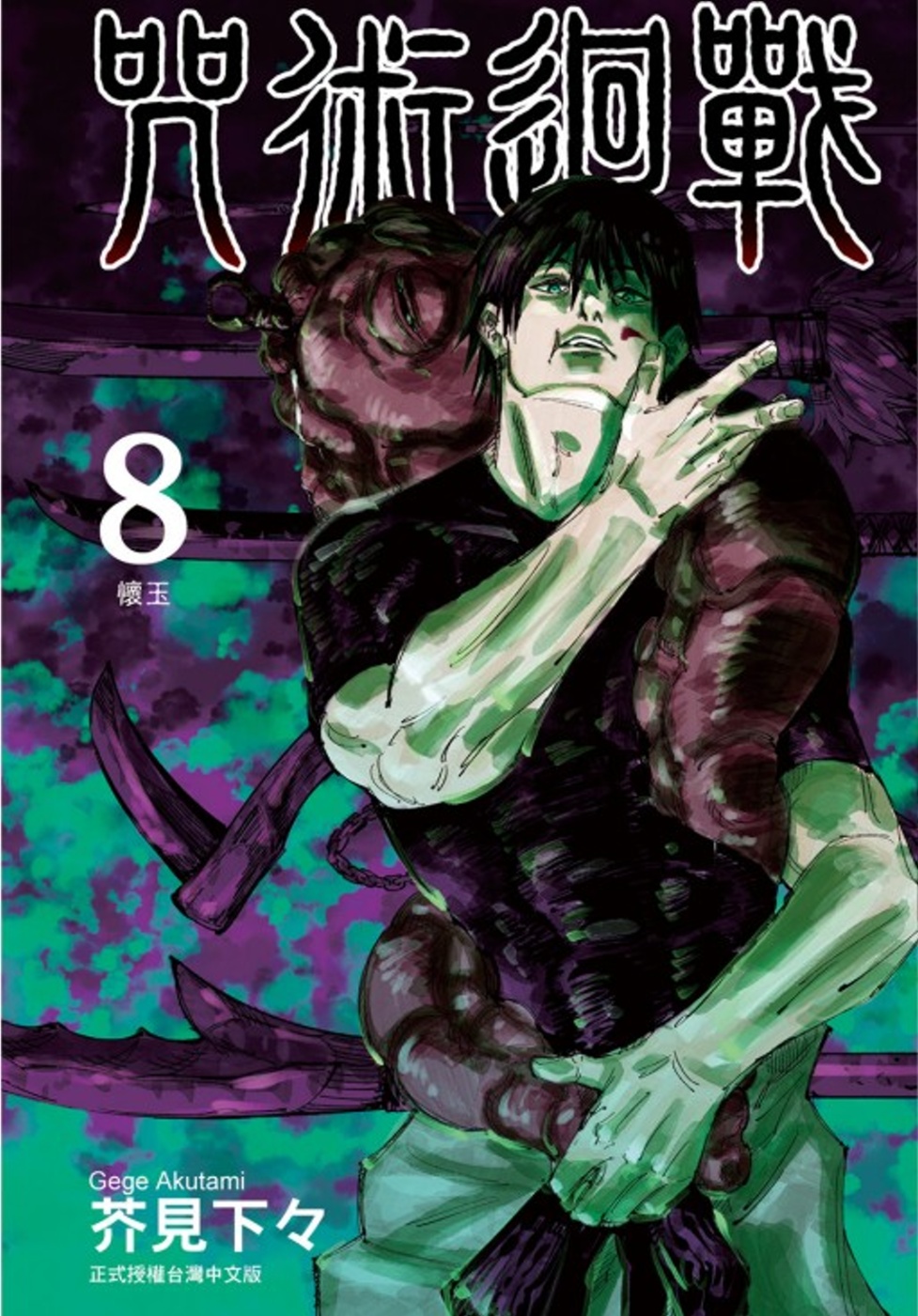 咒術迴戰 8
咒術迴戰 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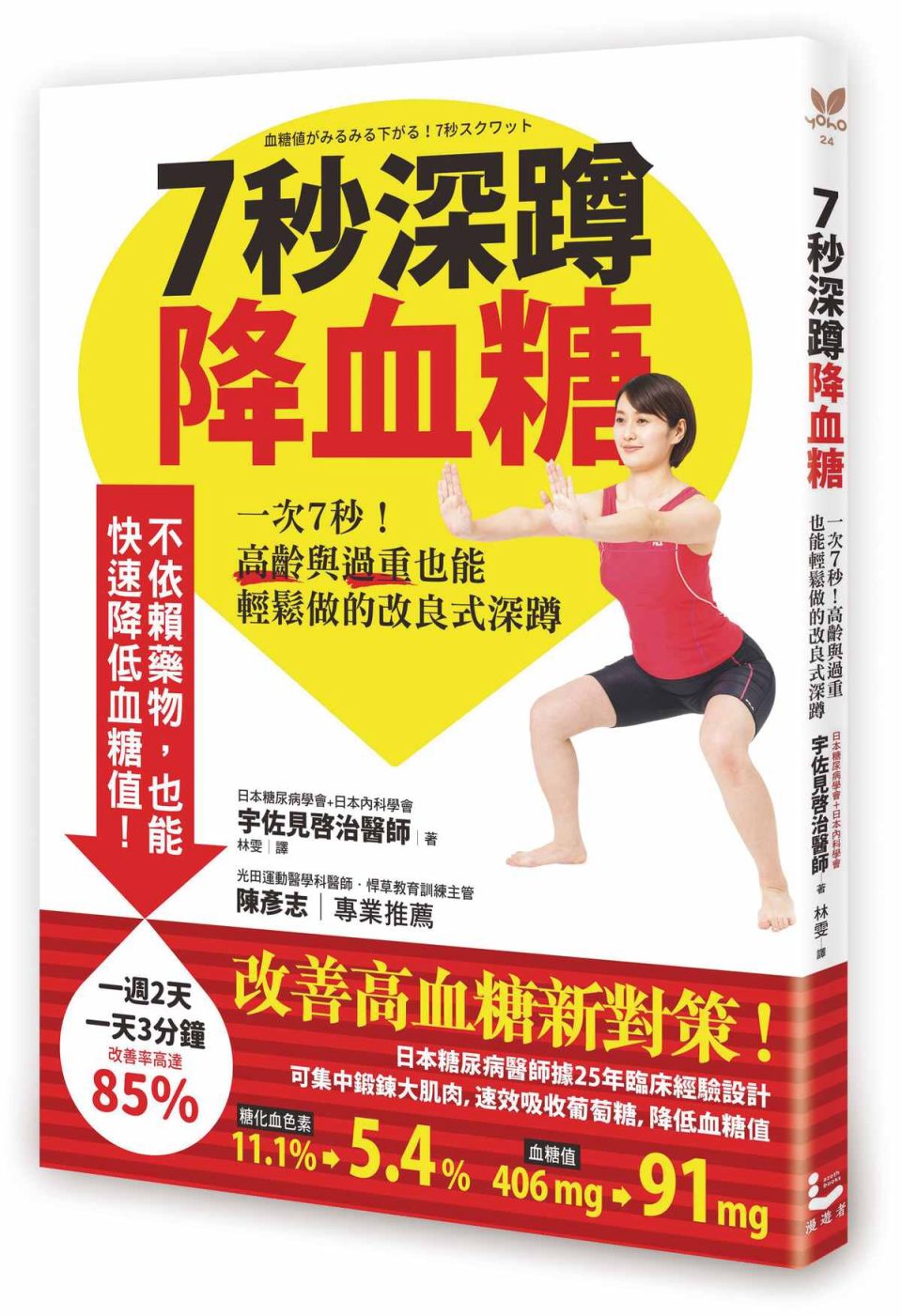 7秒深蹲.降血糖:一次7秒!高齡與...
7秒深蹲.降血糖:一次7秒!高齡與...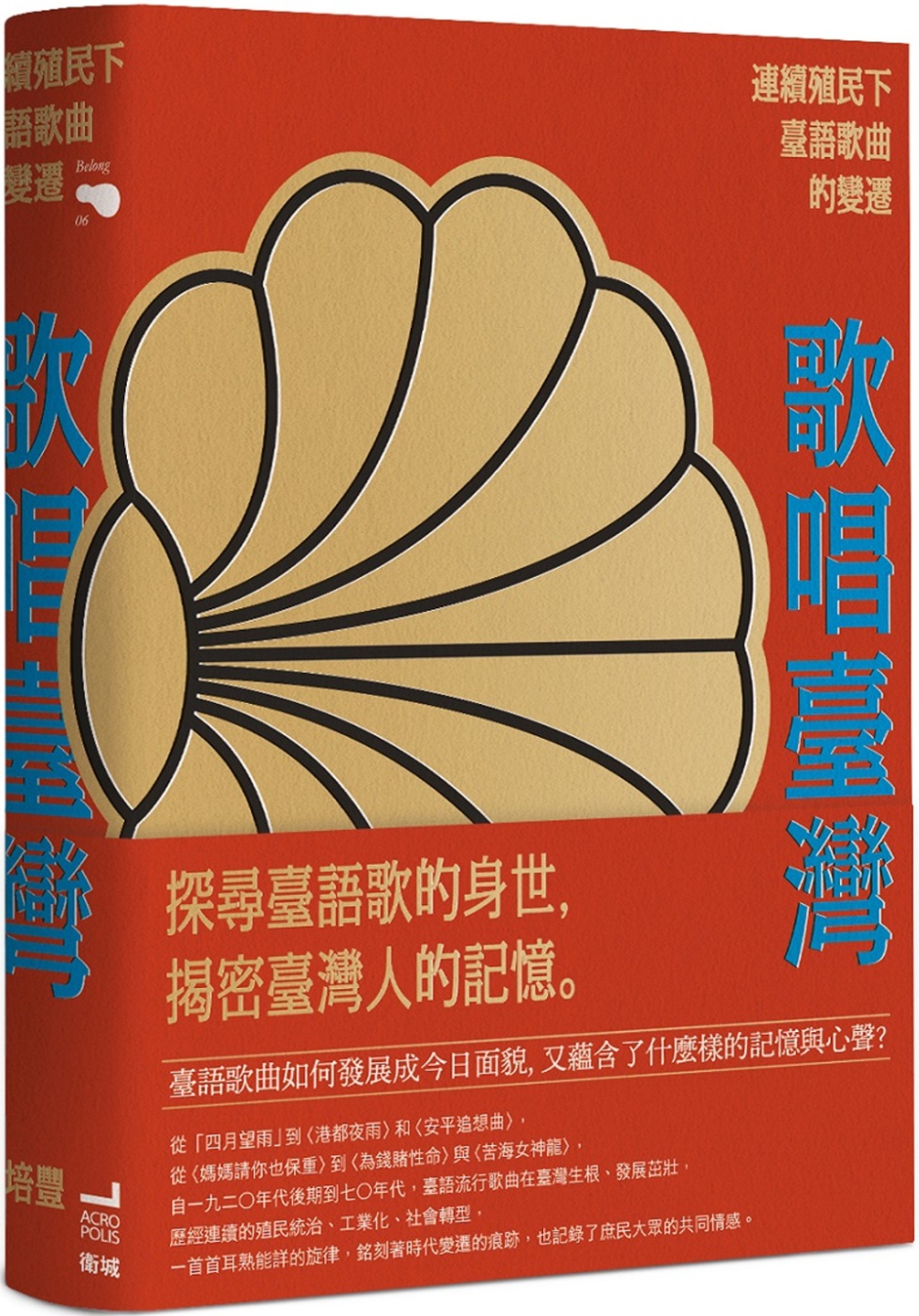 歌唱臺灣:連續殖民下臺語歌曲的變遷
歌唱臺灣:連續殖民下臺語歌曲的變遷 咒術迴戰 14
咒術迴戰 14 咒術迴戰 10
咒術迴戰 1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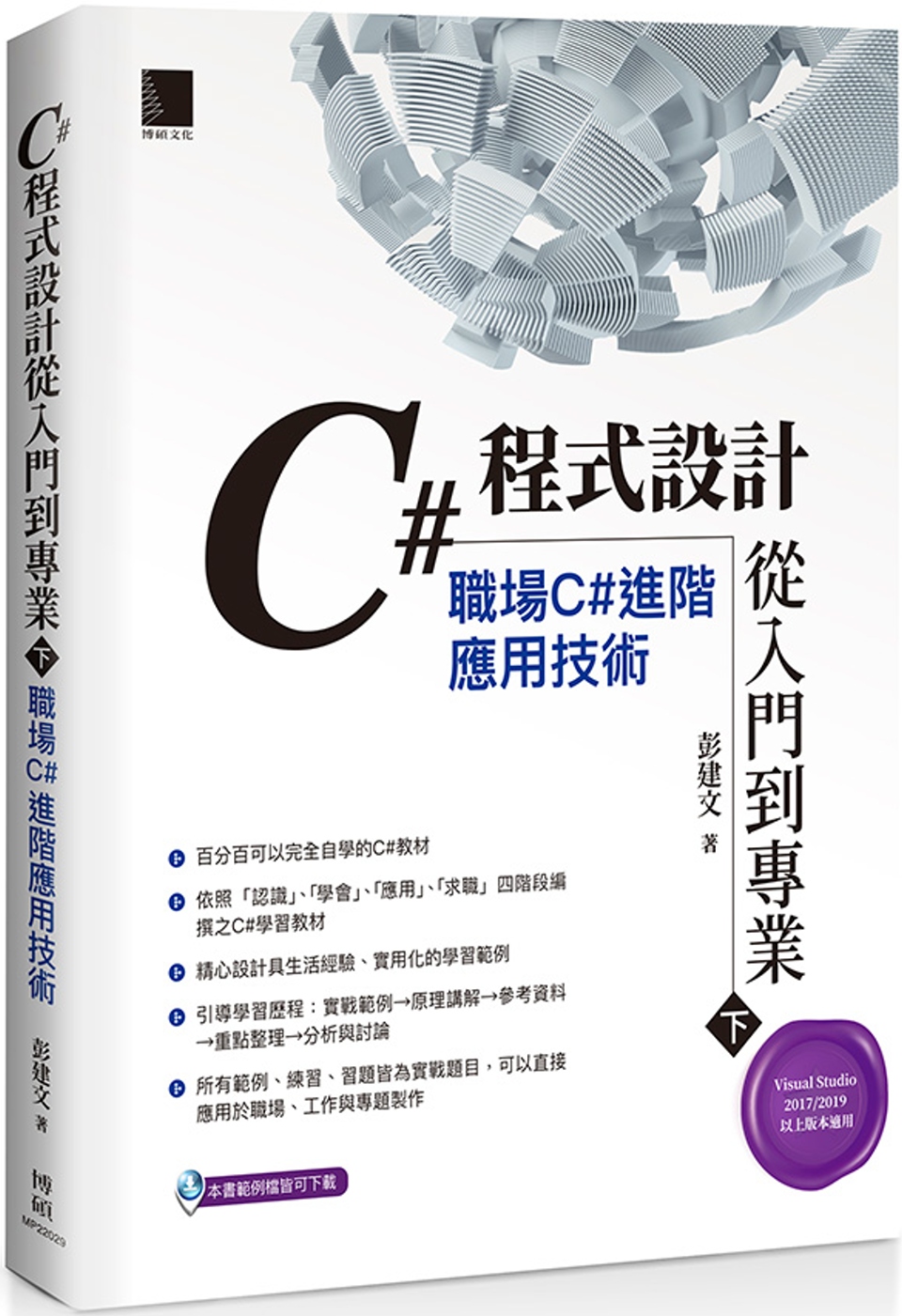 C#程式設計從入門到專業(下):職...
C#程式設計從入門到專業(下):職...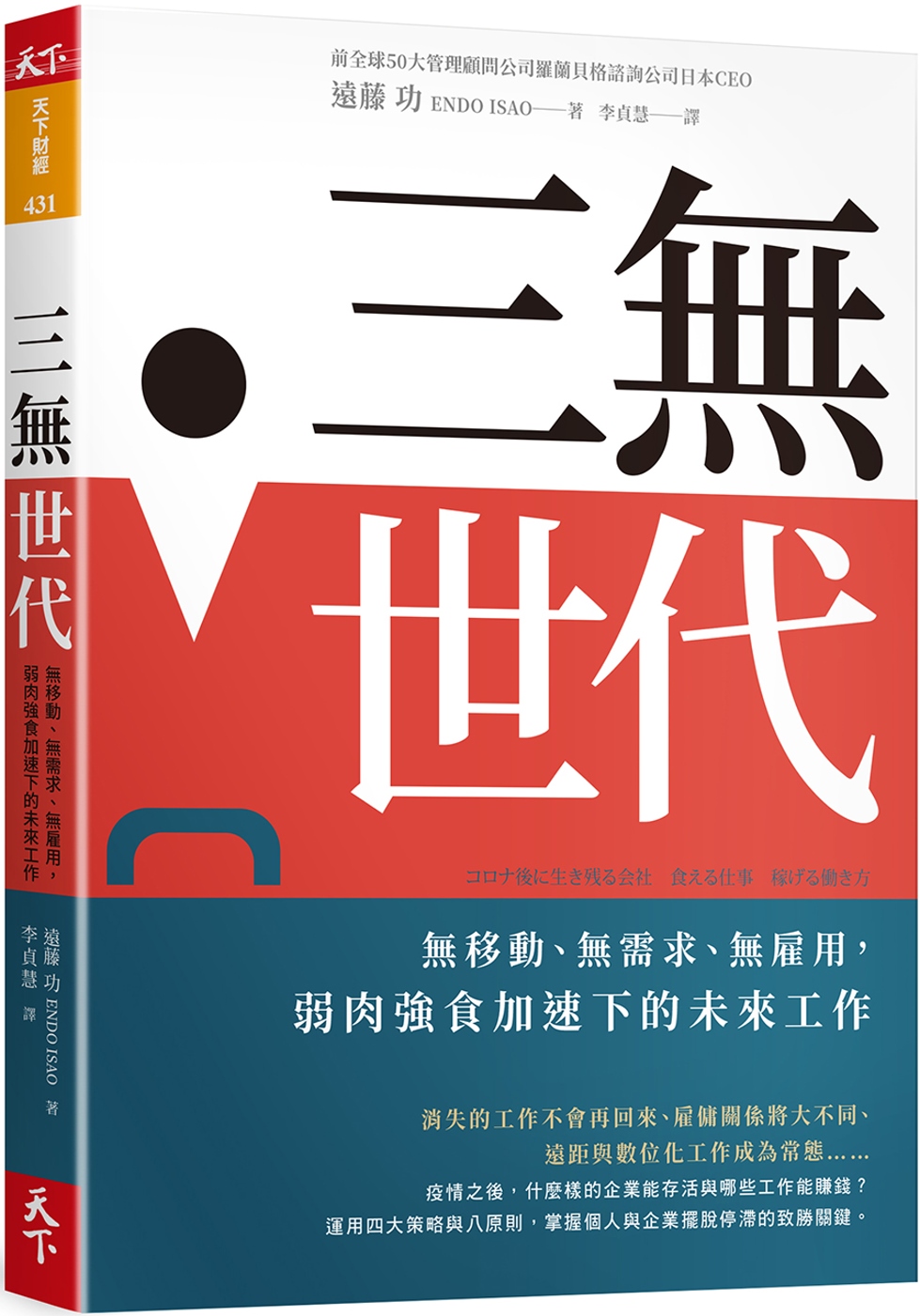 三無世代:無移動、無需求、無雇用,...
三無世代:無移動、無需求、無雇用,... 未來十年微趨勢:洞察工作、科技、生...
未來十年微趨勢:洞察工作、科技、生... 字音字形訓練366(下)
字音字形訓練366(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