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見的城市:全球史視野下的廣州、長崎與巴達維亞 | 運動資訊第一站 - 2024年1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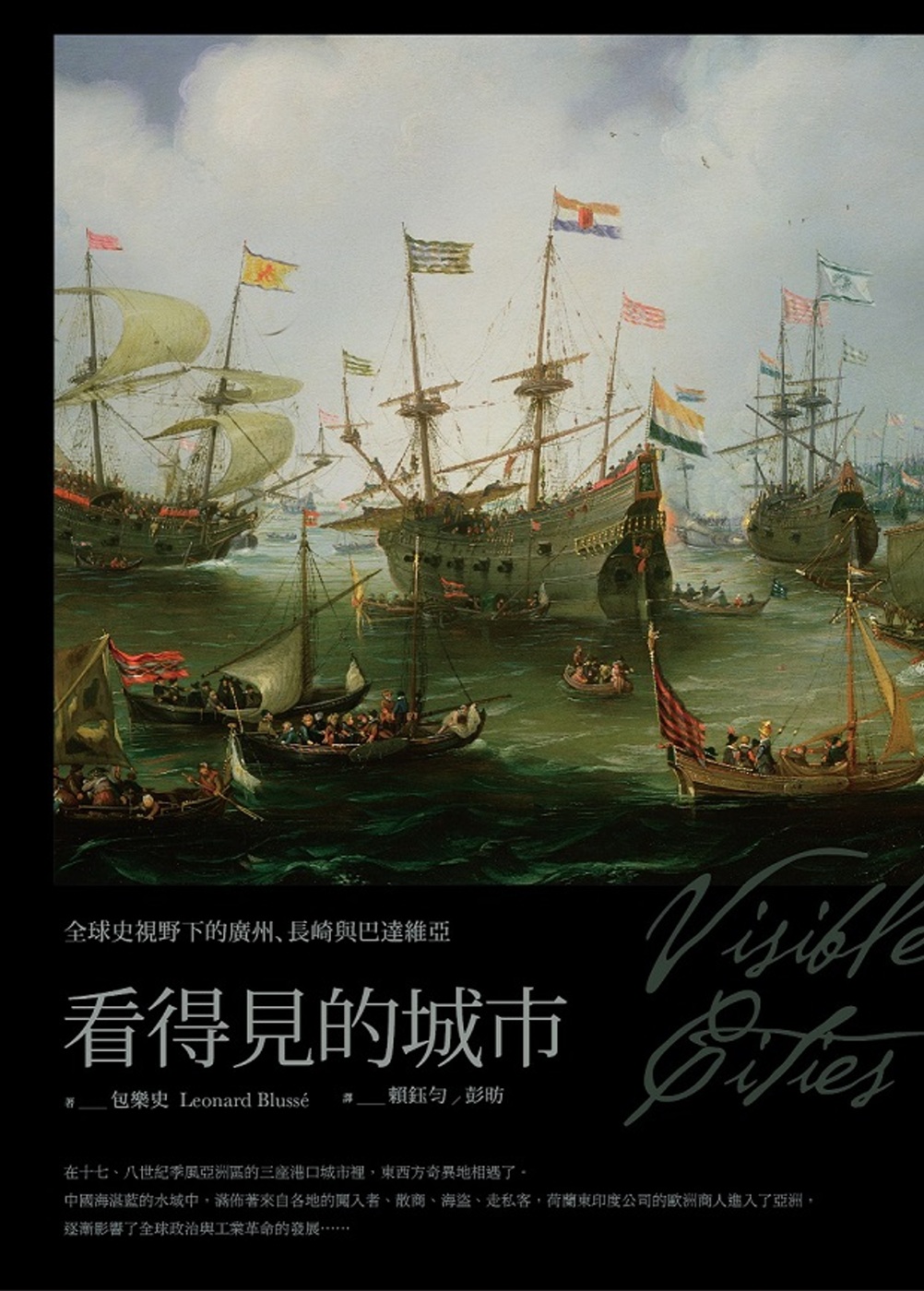
看得見的城市:全球史視野下的廣州、長崎與巴達維亞
這不僅是一部城市史、海洋史,
更是一本視野開闊,敘事精彩的全球史。
在十七、八世紀季風亞洲區的三座港口城市裡,東西方奇異地相遇了。中國海湛藍的水域中,滿佈著來自各地的闖入者、散商、海盜、走私客,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歐洲商人進入了亞洲,逐漸影響了全球政治與工業革命的發展……
荷蘭萊頓大學歷史學家包樂史帶領我們一起回到過去,拜訪十七至十九世紀初期的亞洲最著名的三個港口城市:巴達維亞、廣州以及長崎。在過去,這趟旅行至少要花歐洲旅行者六到八個月的時間。在那些漫漫長夜的航程裡,這三個繽紛的貿易城市,以其超凡的風貌和極具異國風情的魅力,點燃了水手與作家的想像力。它們都留下了為數驚人的文獻和圖像遺產。
相對於小說家卡爾維諾那座「看不見的城市」,作者將巴達維亞、廣州以及長崎稱為「看得見的城市」,因為沒有任何其他十八世紀的亞洲城市,比它們更頻繁地被以圖像與文字描繪。在這三個城市裡,東方與西方以相似卻又極端不同的方式相遇。
作者以全球史的視角討論圍繞著同一片海域的三個港口社會。以廣州、長崎及巴達維亞為中國海一帶人類活動的焦點,比較這三個城市根本的重要差異,並同時考察這三個城市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互動。此外,作者還特別強調人的經驗,唯有聆聽居住或工作於這三個亞洲港口的人們聲音,我們才能對這三個城市有所感受。這些中國人、日本人及荷蘭人,是如何見證他們居住於這些城市的時光?在有限的人生經驗裡,他們又如何反映出這些他們工作、生活於其中的港口面貌?
包樂史認為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是一個全球變遷的時代,對此,中國、日本與爪哇的政權都被迫對這樣的歷史轉變做出回應。相較於以往針對帝國中心所作的研究,書寫這三座城市的跨文化貿易的現象及背後機制,或許更能洞察中國及日本帝國的想法,乃至西方的想法與野心。透過廣州、長崎以及巴達維亞這三扇窗,作者清楚地讓我們認識到這些地區的現代性特色。
作者簡介
包樂史 (Leonard Blussé)
1946年生於荷蘭,早年曾到臺灣和日本進修,荷蘭萊頓大學博士。1977年起在萊頓大學歷史系任教,現為該系教授。他通曉英文、中文、日文、印尼文、荷蘭文和法、德多種歐洲語文。主要專長為東南亞史、東亞史、海外華僑史、印尼華人史、華僑貿易史及全球史。
著作除了荷蘭東印度公司有關台灣檔案及巴達維亞華人公館檔案的編纂外,另有專書《公司和貿易:法國大革命之前的遠洋貿易公司論文集》、《奇怪的組合:荷蘭東印度公司控制時期的巴達維亞的中國移民、混血婦女和荷蘭人》、《歷史的朝聖者:與歐洲擴張史學者們的私人談話》等等。此外,譯為中文的有:《巴達維亞華人與中荷貿易》(1997)、《巴城公館檔案研究:十八世紀巴達維亞唐人社會》(2002)、《航向珠江:荷蘭人在華南(1600-2000)》(2004)、《苦澀的結合: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一齣離婚戲劇》(2009)。其中,《苦澀的結合》曾獲荷蘭「金質貓頭鷹文學獎」(Golden Owl Award),並榮登荷蘭和德國書籍暢銷排行榜。
導讀
序言
第一章 三扇機會之窗
相對於卡爾維諾那座「看不見的城市」,本書將巴達維亞、廣州以及長崎稱為「看得見的城市」,因為沒有任何其他十八世紀的亞洲城市,比它們更頻繁地以圖像與文字被描繪。在這三個城市裡,東方與西方以極端不同卻又相似的方式相遇。
第二章 跨文化貿易的經營
在十六世紀到十七世紀的歷史進程中,由於中、日王朝的更迭以及歐洲人在亞洲海上貿易的擴張,中國海區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在服務於洲際貿易的港口城市裡,我們可以看到區域與全球力量的互動與糾結。
第三章 聯繫分離之地
唯有聆聽居住或工作於這三個亞洲港口的人們的聲音,我們才能對這三個城市有所感受。這些中國人、日本人及荷蘭人,是如何見證他們居住於這些城市的時光?在有限的人生經驗裡,他們又如何反映出這些他們工作、生活於在這些港口中的「人們情況」?
原書注釋
參考文獻
導讀
這是一部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十九世紀通商口岸城市研究所沒有說的故事,說它是前傳也行。談起廣州、長崎與巴達維亞,你會聯想到什麼?一般人可能不太會將這三座城市連在一起。《看得見的城市》談的就是十七、八世紀的中國海區域的這三個港口城,如何扮演著爪哇、中國與日本大多數地區門戶的故事。
我們可以用簡單幾句話涵蓋這本書的大意:「十七、八世紀季風亞洲區的三座港口城市:廣州、長崎與巴達維亞裡,東西方奇異地相遇了。荷蘭東印度公司帶來的歐洲貿易者,伴隨著中國海的私人貿易,進入東亞及東南亞。在這塊遍南中國海湛藍的水域裡,滿佈著來自各地的闖入者、散商、海盜、走私客,這種型態的貿易方式,後來影響了全球政治與工業革命,並揭示了全球發展的區域性影響。」
本書作者包樂史(Leonard Blussé),研究台灣史或海洋史的學者應該都不陌生,他可是國際上著作等身的歷史學家,國內許多研究荷西時期台灣史或中國海洋史的學者,像是曹永和、翁佳音、陳國棟、康培德、劉序楓、鄭維中、李毓中、邱馨慧及查昕等人多少與他有過學術往來或受其著作啟發。包樂史於一九四六年出生於荷蘭,學生時代曾到台灣和日本進修學習漢語與亞洲歷史。一九七二年獲得荷蘭萊頓大學的博士學位,曾任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院研究員及萊頓大學印度尼西亞研究計畫主任,現任萊頓大學歷史系教授。他從中學起,就開始學習各種語言,奠下日後他在研究時,嫻熟地將各種語文如中文、日文、印尼文、荷蘭文及法文、德文運用在寫作中。
包樂史的專長為東亞與東南亞近世史、海外華僑史及全球史。除了大量有關荷蘭東印度公司有關台灣檔案及巴達維亞華人公館檔案的編纂外,著有《公司和貿易:法國大革命之前的遠洋貿易公司論文集》、《奇怪的組合:荷蘭東印度公司控制時期的巴達維亞的中國移民、混血婦女和荷蘭人》、《歷史的朝聖者:與歐洲擴張史學者們的私人談話》、《彌合分歧:荷日關係四百年》等等。其中,翻譯為中文的著作有:《《荷使初訪中國記》研究》(1989)、《中荷交往史》(1989)《巴達維亞華人與中荷貿易》(1997)、《巴城公館檔案研究:十八世紀巴達維亞唐人社會》(2002)、《航向珠江:荷蘭人在華南(1600-2000)》(2004)、《苦澀的結合: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一齣離婚戲劇》 (2009)。
本書為包樂史近年來的最新著作Visible Cities: Canton, Nagasaki, and Batavia and the Coming of the American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簡體字版《看得見的城市:東亞三商港的盛衰浮沈錄》已於二○一○年由浙江大學出版。本書主要是在簡體字的基礎上,重新審訂編輯而成。除了內文的修訂外,最大不同在於我們刪除簡體字版包樂史專為中國大陸讀者所寫的序言,並放回了原先簡體字刪除的英文版前言。此外,原書中的數張海船、城市、地圖及人物圖像,也重新購買版權置於正文中,刪除浙大另外挑選的廣州及長崎的港口圖片。
包樂史有這麼多著作,為何會選中這本?最主要原因是本書內容源自作者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的「賴世和講座」所做的三場主題演講,這三場基本上已經將包樂史過往的研究精華涵蓋在內。本書篇幅不長,作者以全球史視角為我們描繪出一幅十七、八世紀中國海的三港口城市的貿易往來圖像,故事相當吸引人,頗符合我們大眾史學書系的宗旨。
本書一開頭,就透過小說家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的故事,拉開整本書的序幕,也點出了本書主標題《看得見的城市》的特別含意。若和卡爾維諾的小說那座「看不見的城市」相較,作者將廣州、長崎與巴達維亞稱為「看得見的城市」,就是要凸顯出沒有任何十八世紀的亞洲城市,比他們更頻繁地以文字及圖像記載下來。
由於講座的地點是哈佛大學的費正清中心,包樂史認為這個學校的學者,近來似乎忽略了季風亞洲的海洋史研究的重要性;而通商口岸體系的開創性研究正是該校早期推動東亞歷史研究居功厥偉的費正清教授的重要成就,因而在此談論這課題,格外具有特殊意義。
就架構而言,包樂史和近來上田信頗受注目的海洋史著作《海與帝國:明清時代》一樣,很明顯受到布勞岱的「地中海研究」架構影響。這位法國年鑑學派的創始元老的名著《地中海》強調人類社會存在著三種不同的時間量度。歷史時間可分為長、中、短三種不同時段。長時段指的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起作用的那些因素,例如地理空間、生態環境、氣候變遷、社會組織等。中時段則指構成社會生活的主要內容,強調經濟與社會的重要性。第三種為短時段,指的是事件的歷史。換個角度看,就是將歷史時間分為地理時間、社會時間及個體時間。
以布勞岱為仿效對象,包樂史開宗明義地就形容全書是以宏觀的視野引發讀者興趣,然後以關鍵發展當主菜,再以個人的際遇作為甜點來收尾。因而,我們見到,他的首章談著是中國、日本及印度尼西亞群島三地見證了十七世紀的中、日政權的更替之後,廣州、長崎與巴達維亞三港口城市在中國海發展的輪廓。他談論的主要是背景的部分:其中重點有:研究的海域範圍、時間框架、港口城市、中國海上疆域、官方機制、解禁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到來、中國海洋政策的轉變等等。在這部分裡,作者清楚地描繪出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歐洲人在亞洲海上貿易的擴張,中國海域發生的重大變化。包樂史在這些錯綜複雜的海域分流與合流現象中,讓我們見到區域與全球勢力的互動與連結,而最終獲利者,原來是活躍於各地的中國私商網絡。
主軸清楚之後,作為主菜的第二章則處理這三座城市邁入十八世紀後的分歧發展軌跡。包樂史開始讓我們見識到這三座港口城呈現的景象。他關注的問題有:各地政府如何管制並以特殊手法控制這種型態的國際貿易?這些港口交易著哪些商品?
第二章是全書份量最多的部分。在管理方面,到了清朝,廣州的進出口稅收作法有行政上的調整,亦即將稅收事務轉交給公行的商人。在日本長崎,幕府則採取較另外兩地更為實際的作法,也就是以幕府將軍為中心,透過「絲割符政策」控制進口絲價,並設有長崎會所將財務往來收歸在自己手中。
巴達維亞則又是另一種型態,這城市基本上既是荷蘭東印度公司亞洲貿易網絡的前哨站;也是荷蘭殖民帝國的首都。這個有著「東方女王」稱號的城市,在季風亞洲的海域上,統治著一個擴張及貿易的商業帝國。作者不僅談這座城市如何興起,也說到城內曾經所發生過的種族衝突的華人大屠殺事件。至於一般史家較少關注的城市崩壞的故事,這書也提出看法,認為十八世紀末的巴達維亞的熱帶疾病或傳染病,尤其是淤積的河口提供了瘧蚊的大量繁殖,造成每年大量人口的死亡,促使城內居民不得不往內陸遷移。
這部分的故事中,我格外感興趣的是長崎的這一段,或許是受到近來新聞的影響。國際大導演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將日本作家遠藤周作(1923-1996)的歷史小說《沉默》改編為電影,目前正在台灣拍攝部分場景。這故事講的就是德川幕府時代禁教令下,葡萄牙耶穌會傳教士偷渡到長崎傳教並調查恩師棄教的故事。包樂史的重點當然不在葡萄牙,而是繼這他們之後,從平戶移到出島的荷蘭人的故事。
透過長崎,包樂史談到了一般我們所知甚少的日本與荷蘭人打交道的貿易方式。像是絲割符制度、市法商法、小判銀幣、長崎會所、蘭學,或者是荷蘭人到日本後,會找來翻譯團隊,蒐集資訊,寫成「荷蘭風說書」這樣的資料。日本人在沿海水域,做到了中國人在廣州所未能做到的事,亦即幕府藉由控制得宜的權力制衡,徹底掌控了軍事與經濟事務。
包樂史相當擅長綜觀全局,以全球史及比較視角透視這三座城市。他不像那些如《哥倫布大交換》、《槍砲、病菌與鋼鐵》、《一四九三》等書籍過度單一地強調物種交流的重要性,也不像《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一再地強調「笨蛋,問題在制度」,而是將諸多因素一起考量。像「茶改變世界」那一小節,包樂史就提到廣州的貿易如何被單一的茶所支配,不僅加速了英國人對印度的征服,也導致美國的獨立戰爭。當然,在這波的全球衝擊下,荷蘭東印度公司越來越難賣出品質較差的茶葉。多少也就是在荷蘭設置了中國委員會,繞過了過往的這座「東方女王」的轉運功能,改為直接經營荷蘭與廣州間的貿易後,巴達維亞喪失了既有的命運。此外,美國人來到東方的這段故事,雖然不是此時的重點,但也不能忽略其重要性,包樂史也做了頗為精彩的論述。
若說到這部分商品的特色,讀者覺得包樂史只點到為止,還一猶未盡的話,建議可以搭配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維梅爾的帽子》一起閱讀。他是一位相當會說故事的史家,功力與美國著名中國史學者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不相上下,但兩者相較,卜更具有全球史的視野。
卜正民擅長將看似不相干且極為複雜的歷史圖像編織成一張清晰的歷史網絡,凡看過《維梅爾的帽子》的人,應當都會對他所描繪的十七世紀的全球貿易圖像感到佩服。這書的前言〈從台夫特看世界〉一開始就引領讀者走進十七世紀荷蘭小城台夫特(Delft)的歷史時空。因為這個地方正好是荷蘭畫家維梅爾的居住地,而他那些風土人情的傑出畫作中的物品,又是指引我們將歷史考察的視線投向十七世紀全球貿易網的最佳入口。
透過維梅爾的〈在敞開的窗邊讀信的少婦〉,畫中的一只中國瓷盤是一道門,讓我們走出維梅爾的畫室,走向從台夫特通往中國的數條貿易長廊。一五九六年,荷蘭讀者從林蘇荷頓(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筆下,首次認識中國瓷器,他的遊記啟發了下一個世代的荷蘭世界貿易商。十七世紀初,荷蘭人瓜分了原先葡萄牙及西班牙人掌握的中國瓷器貿易路線,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船隻從亞洲運回的瓷器,總數超過三百萬件。這些瓷器對歐洲人而言有如寶物,在歐洲,中國的物品帶來較大的衝擊。東印度公司運回歐洲的瓷器屬於虛榮性消費的昂貴商品,買得起的人屬於少數。受到這股中國瓷器風的影響,以往買不起的人,也開始購買一些台夫特陶工的仿製品。
《看得見的城市》的最後一部份,則舉出幾位精彩人物的探險,呈現出他們生活年代的差異性。這是全書中最引人入勝的一段。這種宏觀中帶有微觀的視角,近來已經成為全球史研究中的話題。
已有學者呼籲世界史的研究者要注意個人的生命史,進而提倡「全球微觀史」的研究取向。近來以《決戰熱蘭遮》一書受到注目的史家歐陽泰(Tonio Andrade) 在〈一個中國農人、兩位非洲青年及一位軍官:全球微觀史的研究取向〉一文中就提出了該如何從全球的視野來寫個人歷史的問題。他舉了三本著作為例,分別是史景遷的《婦人王氏之死》、Linda Colley的《Elizabeth Marsh的嚴酷考驗》及新文化史重要史家Natalie Davis的《騙子遊歷記》。這些著作為了要探討文化間的聯繫及全球的轉變,他們的焦點都集中在一位於不同文化間旅行及探險的旅行者身上。這種研究取向使得這些書都有趣易讀且令人印象深刻,因而擁有廣大的讀者群。歐陽泰期盼世界史家能嘗試以全球的脈絡來研究個人的故事。文中,他講述的是一個有關中國農人、兩位非洲男孩、兩位爭執不休的荷蘭商人及一位中國軍官的故事。所有這些人物都被捲入十七世紀的巨大的跨國貿易及跨文化互動的時代浪潮中。
這樣的故事,我們在包樂史的最後一章也可以見到。
他再次強調布勞岱所謂「個體的時間」的概念。他認為唯有聆聽曾經居住在這三個港口的人們的聲音,我們才能對這三個城市有所感受。這些中國人、日本人及荷蘭人,是如何見證他們所居住的這些城市的時光?在有限的人生經驗中,他們又如何反映出這些港口中工作與生活的人們的日常生活?在中國經驗裡,他舉出了王大海的例子,認為華人對於西方的事物較不感興趣。至於日本人,透過蘭學者,可以看出他們在言談之中,經常提到他們與荷蘭人、西方器物及各種新發明的因緣。
這章最精彩的地方在於透過三位荷蘭人蒂進、多福及范伯蘭的角度來觀看西方人對中國及日本的印象。包樂史並非是在推崇這些人物在那個時代所扮演的決定性特殊角色,而是基於他們正處於一個時代的洪流中,目睹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最後日子,為他們的混亂的生存年代,留下了生動的寶貴敘事。
在全書結尾,包樂史點出了十八世紀九○年代之後,全球變遷的效應因中國南海的貿易而有了轉變,除了英國之外,所有的歐洲遠東貿易者,都因與法國的戰爭而抽離開市場,美國人也很快地取代了他們的位置。簡單地說,歐洲人的失敗就是美國人的成功。要搞懂這段新的故事,如同包樂史所說:「就去讀讀費正清的書吧!」
一如《維梅爾的帽子》所強調的,有時歷史該強調的不在於一邦一國的國別史或區域史,而該將視野擴及幾個大陸間的物品流通。這書進一步引用十七世紀英格蘭詩人兼神學家的約翰‧鄧恩(John Donne)的名言:「人非孤島,無人可以自全」來說明十七世紀的世界觀。在一六二三年鄧恩寫下那首詩之前,世界是一個個彼此隔離的地方,以致某地發生的事,完全不會影響其他地方情勢,但在那之後,人性共通這個觀念開始出現,共同歷史的存在成為可能。鄧恩對十七世紀大陸的比喻,一如佛教的因陀羅網的比喻:每個泥塊、每個珠寶,每個喪失與死亡,每個誕生與生成,都影響了與之共存的每一泥塊和和珠寶。這種世界觀要到十七世紀才得以想像。
同樣地,包樂史這本《看得見的城市》的敘事要較《維梅爾的帽子》更進一步,透過全球史的視野,讓我們看清楚十七、八世紀以來廣州、長崎與巴達維亞這三座港口城市的盛衰起伏。相較於以往的書籍,他不僅強調貿易商品如絲綢、茶等物質文化,更強調背後的地理空間、生態環境因素,更將制度與貿易間的關聯,做了深入淺出的綜述。歷來,我們習慣將台灣史、中國史與世界史作為三個不同發展歷史的區塊,各自論述,我想這三座城市的全球史書寫,肯定為我們立下了最好的示範。
各位讀者看完此書,若對各部分細節歷史有需要再進一步加強的, 建議可以閱讀以下幾本進階版新書:羽田正的《東インド会社とアジアの海》(講談社,2007)、羽田正編《海から見た歴史》(東京大學出版社,2013) 上田信的《海與帝國:明清時代》(廣西師範大學,2014)、以及Adam Clulow的The Company Shogun: The Dutch Encounter with Tokugawa Japa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4)。
蔣竹山(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2015/2/7
「紅毛番」在遠東 爭取中國及日本市場,是一個長期必要而持續的、適應當地環境並需不斷調整的過程。在一封來自荷蘭省長毛利斯(Prince Maurice)的信件獲得大將軍的私人允可之後,一六○九年,第一家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工廠在日本的平戶開設。荷蘭人(以及若干年後尾隨而至的英國人)面臨了強大的挑戰:藉由在澳門與長崎的兩個基地,葡萄牙人在中日貿易間已經取得了幾乎無法撼動的位置。 在其最初十年中,德川幕府(1603—1868)制定了各種策略來緩解貿易上對葡萄牙壟斷者的依賴。因為日本海運在中國是被禁止的,而中國船隻也被明朝政府禁止前往日本,獲得中國貨物的唯一方法,就是給予日本商船稱為禦朱印狀的將軍特許,使之可以前往東南亞與中國商人交易。為此,稱為「日本町」(Nihon Machi)的日本屬地,被設置在臺灣、馬尼拉、印度支那(indo Chinese)海岸的會安(Hoi An)和越南東京(Tonkin),以及泰國的首都阿瑜陀耶(Ayutthaya)。 一六二四年,在大員灣(譯按:今臺灣的安平)入口處建立的熱蘭遮城(Zeelandia Castle),很快帶來了荷蘭人與日本商人的摩擦,導致德川幕府在一六二八年到一六三三年間宣佈了對荷蘭的全面禁運。在這些事件獲得了外交上的處理之後,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理事會得到了這樣的結論——如果公司想繼續在這個驕傲的帝國裡做生意,唯一的選擇就是使在日本的人員全然地遵從當地的規矩和傳統: 公司的人員……首要地必須虛心、謙卑、禮貌、友善,並對日本人極盡親切,由此最終我們會贏得他們的心。「虛心」包含審慎的言行和謹慎的處事,「謙卑」意味著一個人永遠不能以妒忌或高傲的言行面對這個容易受到冒犯的國家,反倒要永遠表現得像是低人一等。「順從」意味著我們不應該違反他們的法律,但也不要顯得膽怯或是遷就,或是用零散瑣碎的方式維護公司的利益。 如同我們接下來會看到的,這些經營之道,遵循著「在日本則行乎日本」的想法,在接下來的那些年裡,成為了任何進一步行動的指導原則,而荷蘭人由此獲益良多。 日本的大範圍海外貿易擴張,和荷蘭與英國的東南亞擴張同時開始,隨後很快地又被幕府的干預打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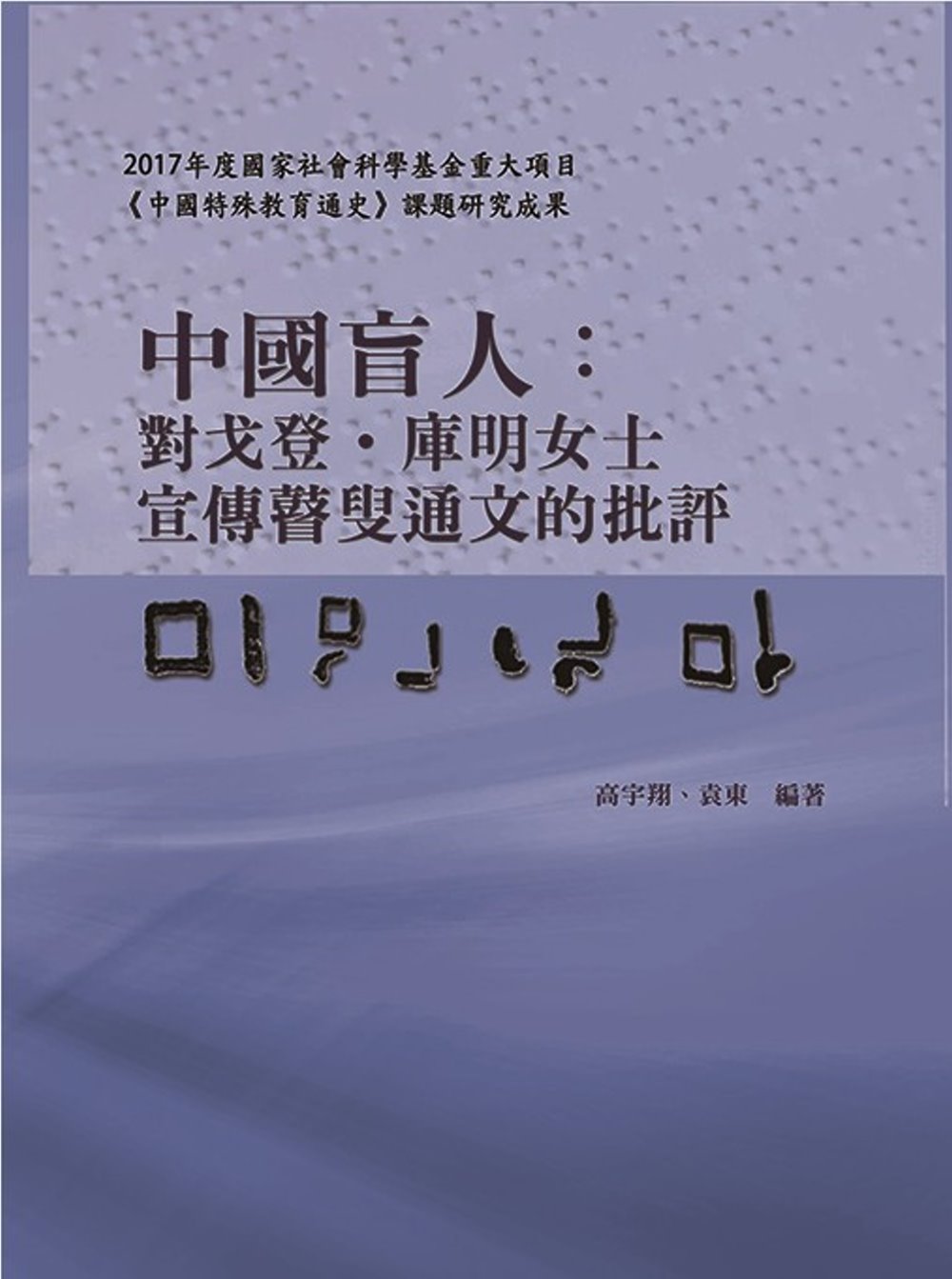 中國盲人:對戈登•庫明女士宣傳瞽叟...
中國盲人:對戈登•庫明女士宣傳瞽叟... 身心同治:一位盲人醫師的感悟心語
身心同治:一位盲人醫師的感悟心語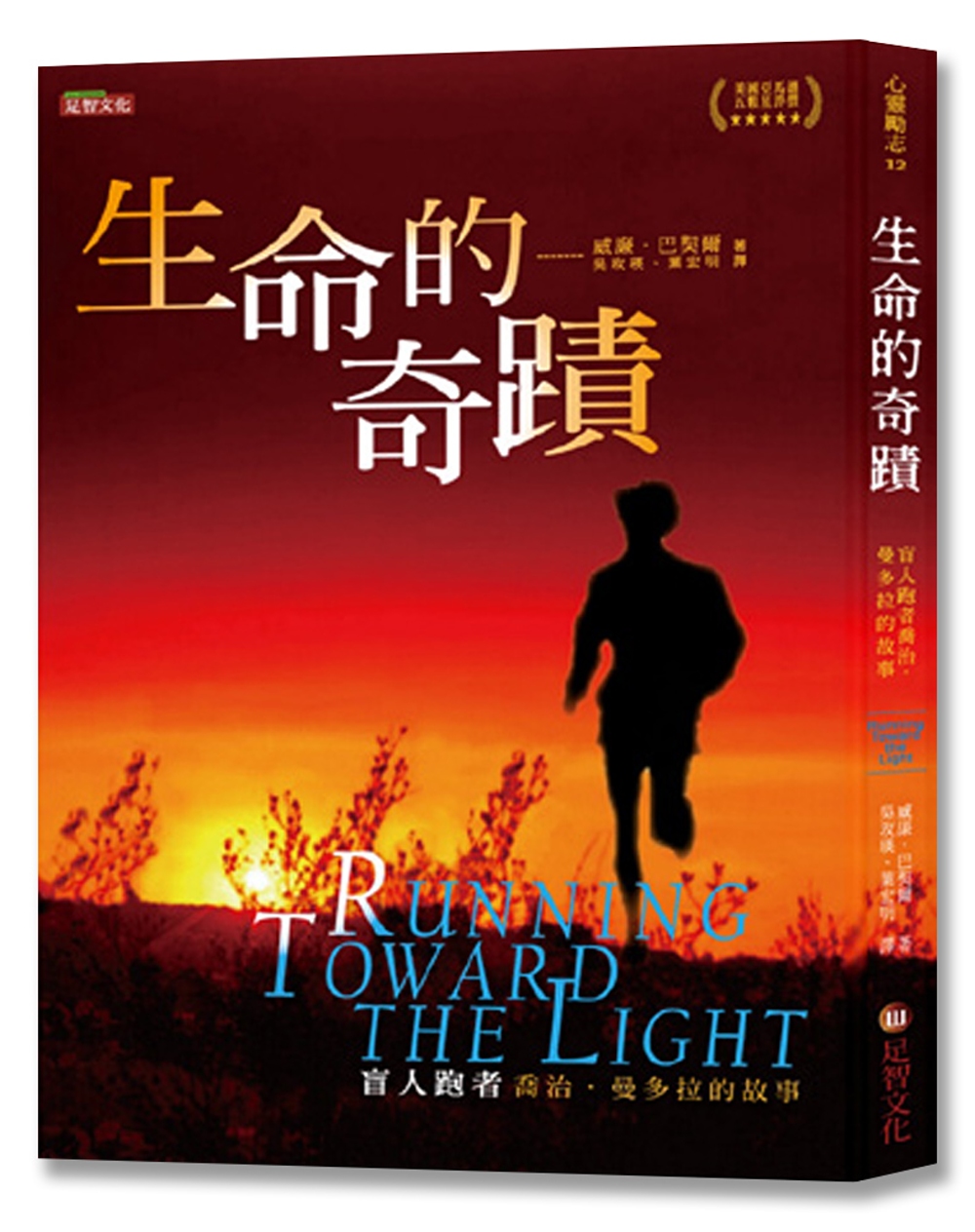 生命的奇蹟:盲人跑者喬治.曼多拉的故事
生命的奇蹟:盲人跑者喬治.曼多拉的故事 盲人鄉
盲人鄉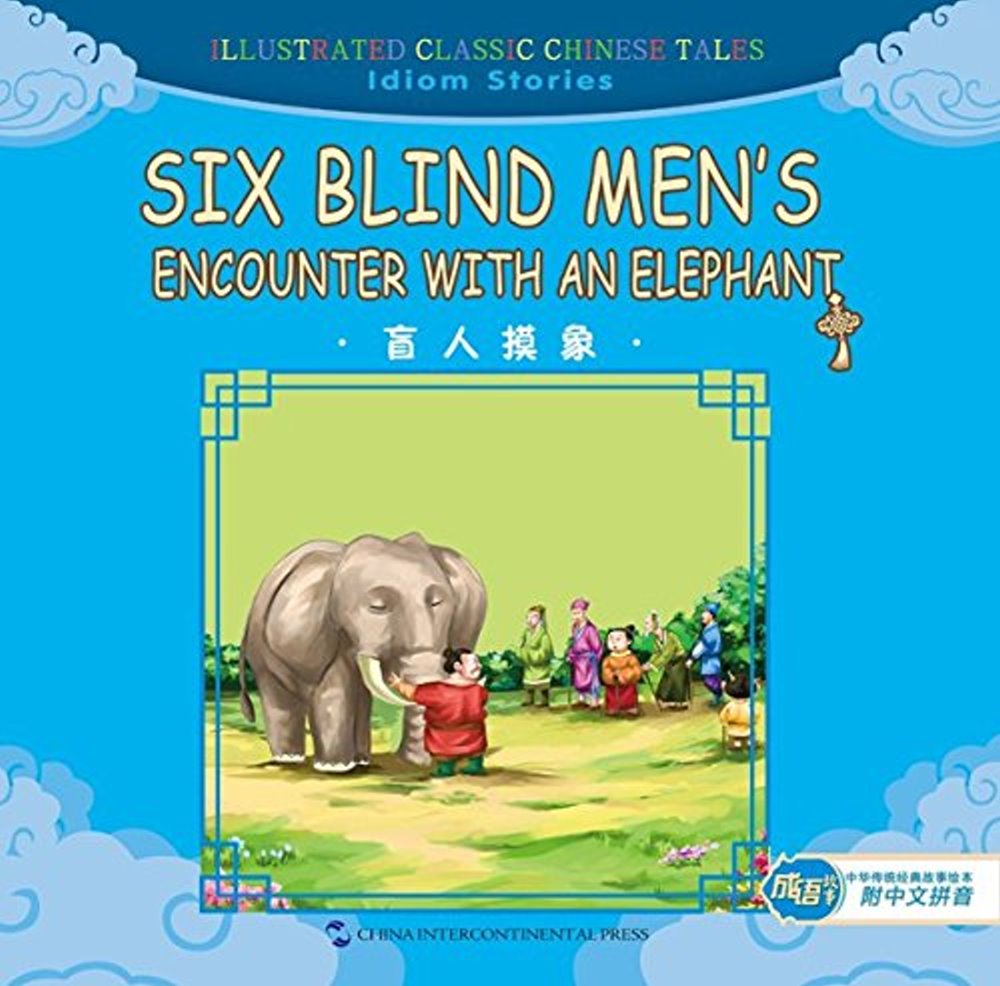 盲人摸象
盲人摸象 盲人奧里翁︰龔祥瑞自傳
盲人奧里翁︰龔祥瑞自傳